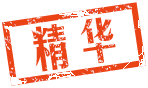|
|
板凳

楼主 |
发表于 2011-8-18 10:54:49
|
只看该作者
3,有一种译法叫救赎
新病的原因豁然开朗后,在全美同时开始了一系列研究和追踪项目,希望能尽快解开这个新病病因的谜团,但是科学遇到了最大的难题:没钱。" c* j8 s3 T/ k6 c
1981年里根上台,他的执政纲领简单到两条:缩减开支、减税。美国政府各部门一下子捉襟见肘,连现有的项目都难以维持,就更别说研究一种主要在同性恋人群中出现的新病了。6 C6 d7 S5 V: L3 V2 L& v. Q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新的疾病主要限于同性恋人群,主流媒体对它还是漠不关心。一些同性恋艺术家站了出来,一方面呼吁加强对这种病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呼吁同性恋者自律,可是这种呼吁基本上是徒劳的,因为广大的同性恋者认为诸如公共澡堂等是他们奋斗了多少年才争取到的权力。与此同时,这个新的疾病终于有了第一个较为正式的名字: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简称GRID。
8 g" J( V w$ C. T. r+ _5 q 1981年,纽约大学医学中心治疗了一位患卡波氏肉瘤的非常英俊的加拿大空服员,在问诊的时候这位叫杜戈斯的人讲述了他在加拿大和美国各大城市的性行为。一年以后,洛杉矶的研究人员确认该市最初的19个GRID病人中有4个和杜戈斯有性行为,另外4个和上述4个人中的某位有过性行为,也就是说,洛杉矶最早的19个病人中的8个人是被杜戈斯传染的。其中一个病人在和杜戈斯发生性行为后10个月才出现症状,另外一位在和杜戈斯共度周末后的第13个月才出现卡波氏肉瘤,证明了研究人员的另外一项很不详的猜测:这个病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潜伏期。
l8 O. Y/ U3 F$ y% j GRID很快在全美一半以上的州出现,在血友病人中也相继出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建议建立新的献血指南,以劝阻同性恋和吸毒者献血和卖血。这个建议受到血友病协会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怕没有足够的血源供给血友病患者。这个建议也受到同性恋组织的反对,认为这样侵犯了他们作为公民的义务献血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负责血液规范化的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只能继续观望。但是所有的人都同意,应该给GRID改一个更合适的名字。8 Z9 o( S# e/ g% p* C& H( i2 M
1982年8月2日,著名播音员丹•拉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里提到AIDS这个词,从此这个新的疾病就被称为AIDS。
! ~8 A. |* K1 t$ V+ w4 u" E8 K 人们在不知道艾滋病的病因是什么的情况下,开始从心灵的角度考虑,AIDS究竟仅仅是一个新的传染病,还是上天给予人类的提示和惩罚?
3 D8 Z' }$ D% z, E1 j3 M% X 在英文中,Aid是救助的意思,加上s成为复数,AIDS也许应该译为救赎。按宗教和哲学的说法,救赎是个人和社会从痛苦和己所不欲的状况下解脱出来。基督教盼望来自神的救赎,艾滋病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救赎?佛教强调靠自身的修行得到救赎,人类通过征服艾滋病是否能够得到救赎?+ o7 S! `/ f, K# ]
但科学还在谨慎中徘徊,研究人员根本就不知道病因是什么,因此只有观望。在观望中,坏的消息越来越多。
7 g V x2 `4 ^; o0 x 1981年,旧金山的一位婴儿因病输了几次血,7个月后出现艾滋病症状。1982年秋,研究人员得知,为这个婴儿供血的13个人中,有一个死于艾滋病。这是美国第一例正式的通过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引发了疾病控制中心和血库之间的一场大战。2 R' ?$ l& G1 @% _+ f
疾病控制中心提议,对所有血液和第八因子制品进行乙型肝炎病毒抗体的检测。血库对此强烈反对,因为这样一来起码每年要花费8亿美元,他们认为不能用一个病例来说明问题。检测乙型肝炎病毒抗体在中国属于常规,因为中国是乙肝大国,可是美国乙肝不多见,而且通过查乙肝抗体,只能提示病毒感染危险性,并不能确定是否患有艾滋病。因此直到1983年初,这项检测才慢慢开展起来。* ~- W) c/ F$ P( [
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很多人是在同性恋者聚会的公共浴室和性俱乐部染上艾滋病的,专家们很快就意识到艾滋病可能通过精液或者体液传播,基于这些材料,政府有关卫生部门希望能关闭这些公共浴室和性俱乐部,但是在同性恋组织的反对下无法实施。
! m* y- }! V; E3 t, Q" w 随着病例的渐渐增多,媒体上的报道也多了起来,由于对艾滋病所知甚少,公众的恐慌也越来越厉害。尽管公共卫生部门再三强调,正常的接触是安全的,但是还有不少人把艾滋病视为黑死病一类的瘟疫,甚至一些医生拒绝治疗艾滋病人。一些牧师也旧调重弹,宣称这是上帝的意愿。八十年代初的美国,有些草木皆兵的感觉。曾有一位中国比较著名的医学专家来美访问,在饭店里什么也不敢摸,上厕所的时候象老农一样蹲在马桶上,很有些遭洋罪的感觉。
8 s5 \, w6 p) F4 B1 _$ D5 ? 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引起艾滋病,成了专家和民众都迫切希望知道的东西,美国国会在里根政府没有要求的情况下,特拨1200万美元进行艾滋病研究,以期尽快找到艾滋病的罪魁祸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有效的检测方法。
- @ O6 h9 V z( Q% Z( ~' K) u 其实,寻找艾滋病病源的竞争早已开始了。$ D% r1 M. h( t: q' R
在大洋彼岸的欧洲,因为非洲的病人通常到欧洲求医,艾滋病从七十年代末就已经出现了。最初的三名艾滋病病人出现在巴黎的医院里,他们都是来自中非或者在中非待过,而且都患有卡氏肺孢菌性肺炎。和美国的研究人员不同,法国的研究人员并没有将艾滋病和同性恋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三个人一名是异性恋,另外两名是妇女。但是比美国研究人员领先的是,他们一开始就认定是病毒引起的。
% P5 r4 A% K) r1 n( h3 @ 因为肿大的淋巴结是早期的一个症状,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从这里下手成功的机会最大。1983年1月他们取下一名艾滋病病人的淋巴结,使用一种新近建立的培养逆转录病毒的方法进行培养。3 Y, k, x' h2 j
逆转录病毒是一类进入人体细胞后,借助人的细胞的成分来繁殖自身的病毒。美国国立卫生院(NIH)的罗伯特•盖洛在1976年建立了这种将病人血液样品和人正常T细胞共同培养的方法并成功地分离出包括HTLV I和II在内的几种逆转录病毒。法国人认为艾滋病毒和HTLV病毒是一类的,他们预料,如果有病毒繁殖的话,培养液中的T细胞应该疯长。
0 {+ d7 R3 w0 g4 Y- S6 V 但是事实恰恰相反,18天后放射检测法证明有逆转录病毒快速繁殖,可是T细胞却大量死亡。法国人认定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病毒,他们将之取名为淋巴相关病毒,简称LAV。他们随后成功地在几名艾滋病病人身上发现相同的病毒,但是该项目的负责人、巴斯德研究所肿瘤病毒室主任鲁克•蒙特尼尔还是不能确定病毒的分类。5 N$ Z' w. r6 v" {2 D& R A0 V8 n6 O( J
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卫生科学统一服务大学的研究人员相信艾滋病是由某种现有的病毒引起的,他们罗列了一张嫌疑犯名单,HTLV I和II排在首位,这两种病毒的发现者盖洛也坚信或者是HTLV I和II,或者是另外一种相关的HTLV病毒。0 U9 o; T5 z; c( L8 g# h
和为人谨慎低调的蒙特尼尔相反,盖洛为人锋芒毕露,也的确才华横溢。他建立的逆转录病毒分离培养的方法打开了一扇门,使病毒家们得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盖洛是那一代急功近利的科学家的缩影,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择手段,他发现的所谓白血病病毒被证明是因为样本被污染了,他还经常贪他人之功为己有。盖洛本人想得诺贝尔奖想疯了,从1974年开始就游说诺贝尔奖评委,并努力消除对自己的负面报道。; T, w k! n) A- _
1983年5月的《科学》杂志上,有两篇显著的文章,一篇是盖洛本人的文章,另一篇的盖洛的马屁精、哈佛大学爱克斯的文章,反复强调HTLV是引起艾滋病的病毒。在这期杂志上还有一篇文章,是蒙特尼尔关于LAV病毒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0 ~1 M% w, L7 \+ Y1 `$ U+ |
一来是盖洛和爱克斯的文章风头太大,另一方面是因为蒙特尼尔匆忙之间忘了写摘要了。作为审稿人之一的盖洛很热心地帮他写了摘要。满心感激的蒙特尼尔也没有仔细看一下,结果他文章的摘要被张冠李戴地写成了支持盖洛的HTLV理论。
2 I h f8 V1 a 1993年12月,盖洛向《科学》杂志提交了自己的论文,宣称发现了HTLV相关的艾滋病毒。5 q6 M* g T7 w3 V |: B3 S7 v
1994年4月23日,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举行新闻发表会,卫生和福利部长希克勒在会上宣布盖洛发现了艾滋病毒,命名为HTLV-III。在会上满面春风的盖洛展示了新病毒的照片。此后用HTLV-III,盖洛建立了艾滋病血液检测方法,从技术上解决了发现病毒感染者和筛查血液的难题。
- t: A( q0 O9 K9 I( d; c C3 H; n 盖洛成了大明星,美国各地的知名教授们赌咒发誓地捧盖洛的臭脚。在同一天,盖洛在专利局为艾滋病毒注册了专利。5月17日,私人公司开始申请用这种病毒研制诊断试剂,一年后,专利局批准了盖洛的申请。该专利的价值是每年一亿美元的销售和盖洛等人10万美元个人年收入。盖洛名利双收。
# H+ }( z; R. V8 o; B1 [/ ~ 新闻发表会之后,法国人立即提出抗议,理由很简单:盖洛在新闻发表会上展示的照片居然是蒙特尼尔的。, w, [: j, _- a: o3 g7 c
当人们听到这个指控时,都觉得是个笑话。
+ h# p6 c' G1 u' W) p* g |
评分
-
查看全部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