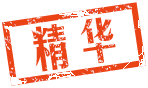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xiejin77 于 2025-10-2 11:11 编辑
* s& o/ v- G: z4 L! k: Y9 W) i
! S1 q8 S4 x+ J5 Y1 j' }1 j2 T5 Y三十六岁的火焰与寒冰——方志敏与瞿秋白的遗著读后 , [5 n5 i- D+ N; L9 Q5 f4 P: K
/ `9 ?4 O2 k* p7 F
( v# h$ a- O9 F4 Y% W引言
1 w& D& m' b/ I, D4 z% j% K
/ c/ Q0 L7 V8 ? A% I5 Z6 y6 u0 u1935年,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得几乎令人窒息的年份。在内部,遵义会议的召开虽确立了新的领导核心,但其背景本身就是对过往路线失败的痛苦修正;在外部,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围剿”的炮火中失守,红军主力仓皇转战,踏上了那条后来被称为“长征”的、前途未卜的艰苦道路。整个革命的前途,似乎都笼罩在一片挥之不去的阴霾里,每一天都可能是末日。
, |3 \& q3 ^# ^$ _就在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口,两位中共早期的杰出人物——方志敏与瞿秋白,命运仿佛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竟在同一年被捕,同一年牺牲,生命都定格在了风华正茂的36岁。每当读到这段历史,我总忍不住去想,这样惊人的巧合,究竟为后人留下了一道怎样的谜题?它不仅仅是两个个体的悲剧,更像是历史本身留下的一组深刻的对偶句,等待着后人去解读其间的微言大义。 ( z; r5 ]/ p- z6 x4 W
身陷囹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都选择了用笔作为最后的武器,留下了文字。一个是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另一个是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然而,将这两部作品并排放在一起,那种精神内核与情感基调上的天壤之别,几乎让人心头发颤。《可爱的中国》是一团烈火,是一曲献给未来的高亢赞歌,字里行间燃烧着革命者矢志不渝的乐观与激情,对那个他未曾得见的新中国充满了滚烫的憧憬。反观《多余的話》,卻像一块寒冰,是一份异常沉痛、近乎冷酷的自我解剖,记录了一个文人革命家对自己“历史的误会”的身份的怀疑和对过往生涯的无情反思,其坦诚与忧郁,读来令人扼腕,长叹不能自已。 * K( l: c8 q1 S; Y& q# Q" R% f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般冰火两重天的巨大差异?若仅仅归因于个人性格,未免失之浅表。追根溯源,答案并非飘忽于个人心性,而是深植于他们迥异的阶级土壤与革命实践的现实大地之中。我更愿意相信,这背后是他们各自的阶级出身、革命实践,以及由此交织成的物质与精神世界,最终在他们临终的笔下凝结出的不同形态。 $ w6 f: D0 a; c
5 l4 A( K& [# T
曾经细细的品读了这两部伟大的著作,心情激荡之余也做了不少笔记。也正是基于此写了这篇文章,我将尝试循着历史唯物主义那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核心路径,去探寻这两位革命者迥异的人生轨迹——那充满泥土气息的斗争与那弥漫着书卷气息的求索——是如何塑造了他们截然不同的临终意识,并最终为我们留下了这两份在中国革命史上分量独特、缺一不可的精神遗产。 7 Q, g: X4 [, N( U+ K% \. K# L# B6 t$ ~
一、 革命道路与阶级烙印:两位战士的生平分野+ a0 E2 u1 X3 \% ^
4 G% N& L& y% k/ R: O5 V0 i
1.1 方志敏:从土地中走出的“农民大王”' z( ^9 Y: G" o9 s/ T
8 j7 H: q0 }# W/ C
阶级出身与早期形成 . K. p7 O( w% ?% e8 f' U3 e
方志敏的革命意志,可以说是在中国农村那尖锐得几乎能滴出血的阶级矛盾中淬炼出来的。他生于江西弋阳的一个贫苦农家,这种出身,让他对地主官僚的压迫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融入血液的切肤之痛。他所成长的环境,是一个被高利贷、苛捐杂税和宗族恶势力死死缠绕的窒息空间。他笔下的县衙门官吏,是“一伙会吃人的豺狼老虎”——这不是文人想象中的修辞,而是他和他乡亲们血-淋的生活体验。这份根植于土地的、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是他日后革命立场最坚实、最无可动摇的底色。他的革命,不是从书本里读出来的抽象概念,而是从生存的绝境里、从无数农民的血泪中嘶吼出来的。
, L- L S0 y; U有一个例子极能说明他转变之彻底:为了推行农民运动,他曾亲自下令处死带头对抗农会的五叔方雨田。即便是祖母和父亲双双跪地求情,也未曾动摇他分毫。这一举动,在注重血缘宗族的传统伦理看来何其“无情”,甚至“大逆不道”,但恰恰说明,他已经彻底完成了从一个宗族个体到一个纯粹的阶级战士的蜕变。这是一种痛苦的“重生”,他亲手斩断了束缚自己的旧伦理的脐带,从此只为那个被压迫的新阶级而活。其立场之坚定,不容任何私情的羁绊,其坚如石,其白似骨。 8 l9 h* ]$ f! E
革命实践出的根据地创建者 r2 w+ r; V! T
方志敏的革命生涯,不是在机关的会议室里规划出来的,也不是在报纸的社论里写出来的。他是在赣东北的红土地上,靠着“两条半枪”的家底,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闹起来的革命。他最核心的贡献,是作为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这不只是军事割据的成功,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实验。他领导制定《临时土地分配法》,把土地——农民的命根子——实实在在地分到农民手里,这种物质利益的直接给予,赢得了农民最朴素也最坚定的拥护。几乎可以说是后来土改政策的渊薮。 : B- a; ^. y' ^8 _
尤为关键的是,在戎马偬偬的战争间隙,方志敏的革命实践并未局限于军事一隅,更展现出一种非凡的、带有创造性的经济才能。他面对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创造性地设立了“对外贸易处”,将根据地的土产输送出去,换回紧缺的盐、布和西药,甚至发行红色股票来筹集资金。这些举措,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马克思主义在他手里,不是挂在墙上的教条,而是解决吃饭、穿衣、打仗这些现实问题的趁手兵器。也难怪毛泽东会高度评价他开创的根据地为“方志敏式”的典范,因为这代表了一种理论与本土实际完美结合的典范。 4 w* D; U7 m$ r0 i r- a) k
领袖与事业的融合
/ R) @% ?, J% P1 h8 Q在长期的斗争中,方志敏的个人身份,已经与他所缔造的事业、与赣东北数百万民众的命运,完全融为了一体。他以“清贫”为信条,这不仅是个人品德的体现,更是一种与国民党官僚的骄奢淫逸形成鲜明对比的、极具号召力的政治宣言。他的母亲和婶婶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只为讨点钱做条裤子、买点盐,他却含泪拒绝,因为他自己分文不取,“当的是穷人的主席”。这种公而忘私,这种近乎残酷的自我要求,在今天看来,显得格外沉重了一些,但也正因此,才拥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 A8 z5 O' T1 e( W: q9 I$ v6 Z这种精神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得到了最极致、最悲壮的体现。当他率部掩护中央红军转移失败,本人已经脱险,却为了寻找失散的大部队毅然返回重围,说出“在责任上我不能先走”时,这个选择最终让他走向了囚笼和刑场。个人的安危,在革命的集体责任面前,被他视若无物。他的肉体,已经成为了革命事业的一个可以牺牲的组成部分。 , n! u6 Z2 U8 T& i, ?1 J% s0 X
可以说,方志敏的革命意识,是在改造现实世界的具体活动中,一砖一瓦、一枪一炮地建立起来的。他在赣东北亲手缔造了一个新社会的雏形,理论与实践之间毫无缝隙。所以,当他走向生命终点时,他的思绪自然而然地超越了个人得失,飞向了那个他为之奋斗并已亲眼见证的未来。他的遗著,必然是那个新世界的宏大投射,是他未竟事业的延续。 : e$ Y% ^/ c/ j# ]. M
1.2 瞿秋白:在书斋与政治间徘徊的理论家6 \. Z/ t. P9 a0 n
$ v* \- T. i( B+ q- y- D; t
阶级出身与知识分子式的形成 % M6 I! Y; t/ k' o1 m
与方志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瞿秋白。他出身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书香门第给了他文人的敏感细腻和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但家道的中落又让他过早尝尽了世态炎凉和寄人篱下的屈辱。这种没落士大夫的身份,给他带来了一种深刻的心理矛盾:一方面对旧秩序充满鄙夷,一方面又难以彻底摆脱其文化习性的影响。母亲因贫病交加、无力维持家庭而自尽的悲剧,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也成了他批判旧社会的个人情感起点。他的革命之路,是一条典型的、充满彷徨与求索的知识分子探索之路:从投身五四运动,到加入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再到作为记者远赴革命初期的苏俄寻找“火种”。他的转变,首先是思想上的、理智上的,是在比较了各种主义后作出的理性抉择,而非源于直接的、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
# F( J/ P7 S9 ?8 @) V革命实践的角色主要是高层理论家与路线斗争
# F8 N) I! c8 t& R7 z" `% q瞿秋白在党内的角色,主要是理论家和早期最高领导人。他的贡献巨大,但多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他最早翻译《国际歌》,让这首全世界无产者的战歌响彻中国;他主编《新青年》等重要刊物,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为早期中共的理论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在数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扮演核心角色,两度在危急关头主持中央工作。他的日常,是伏案于书斋,分析复杂的阶级关系,起草党的决议,与党内外的各种思潮进行理论斗争。然而,这种远离炮火硝烟、充斥着路线辩论和人事纠葛的高层政治,其复杂与残酷,与他骨子里的“文人”气质,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几乎无法调和的矛盾。后来他在《多余的话》中坦言,自己当上中共领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这句看似自谦的话,实则蕴含了无尽的苦涩。 $ E2 _+ F! ~4 ]8 c- s# z
“文人”与布尔什维克的内在冲突 & ]! M3 R0 m" `& O
瞿秋白一生的悲剧性,似乎就根植于他内心深处“文人”气质与布尔什维克战士身份要求之间的持续冲突。他天性敏感、内敛,情感丰富,甚至在政治斗争中显得有些优柔寡断。他在《多余的话》里做了无情的自我剖析,承认自己有“弱者的道德”,害怕争论,总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他甚至坦白自己难以对敌人产生“彻骨的仇恨”。这样的性格,显然不适合做一个疾风暴雨式革命政党的铁腕领袖。
. Y! s) N5 `9 _' `8 z" Z, U这场内心的战争是极其痛苦的,他必须“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用学来的、理智上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去“创造新的情感”。这在某种意义上讲,已非简单的‘扮演’,而是一种长期的、消耗心神的‘自我规训’。他必须用布尔什维克的理论理性,时时看守并鞭策着那个属于文人的感性自我。革命领袖的身份,于他而言,是一件必须穿上的、沉重而冰冷的铠甲,而不是与自己血肉相连的皮肤。他与鲁迅的深厚友谊,以及后来投身左翼文化运动,或许更能安放他那颗文人的心。在文学的世界里,他才能找到片刻的喘息,回归那个更真实、更自在的自我。
5 w5 T+ @# n$ J3 x4 O瞿秋白的人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意识形态认同与个人心理构成之间的深刻矛盾。方志敏的革命角色是他生命经验的自然延伸,是“我是谁”的最终确认;而瞿秋白的角色却要求他不断地、痛苦地否定和压抑“我是谁”。当他在狱中被“完全被解除了武装”,不再需要扮演任何角色,只剩下自己时,那个被压抑已久的、内省的、充满怀疑的知识分子自我,便如潮水般破茧而出。他的遗著,因而成了一种决绝的剥离,是剥去层层政治角色的外衣,向世人展示那个复杂、矛盾的真实个体的最后努力。
2 ~2 y7 N, K/ ?& W, d5 N* i二、文本中那两种截然不同的最后心声; ^9 L5 r, X& e
T, T& S1 `% J1 t1 z$ l
2.1 《可爱的中国》:献给未来的革命乐观主义赞歌
- I8 n% o# f# W5 e/ |
d% G. b, Z3 i6 u《可爱的中国》,通篇文字犹如一首献给未来的史诗,每一个字都在燃烧着炙热的情感。其语言铿锵有力,质朴而又饱含深情,几乎找不到深奥的理论术语,却拥有着雷霆万钧的力量,极具感染力和政治宣传的价值。这不像一个将死之人的哀叹,反倒像一位指挥员在发起总冲锋前的最后动员,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与确信。 ; _; U$ L2 p, D N! H0 s& V6 M8 L
文章的核心,是对一个独立、富强、光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无限憧憬。他先是痛陈祖国母亲被帝国主义蹂躏的苦难,用“地图上染着我们羞耻的血迹”这样的句子唤起国人的共鸣。随后笔锋一转,用极大的篇幅、以近乎狂喜的笔触描绘未来的“可爱的中国”——那里“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工厂林立,田禾丰饶,人民安居乐业,“监狱和法院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这份愿景之所以如此坚实、如此具体,正在于它植根于作者在赣东北苏区的亲身实践。他已亲手建设过一个新中国的雏形,因而这份信念不是空中楼阁式的空想,而是基于成功实践的科学预见和逻辑延伸。 8 T8 @& v( E6 Z* Q
在《可爱的中国》里,作者方志敏的“我”几乎完全消融在了“我们”的集体之中,个人的生死存亡,似乎无足轻重,甚至不值一提。他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在这里,“我”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作为阶级一员的“我们”所为之奋斗的真理,却是永恒的。这篇文章,是他最后的政治工作,是从狱中向外界投出的一柄思想的武器,是一份留给党和人民的、充满信心的政治遗嘱。
5 r6 z9 ^2 i7 ?) [0 d+ d2.2 《多余的话》:一个“历史误会”的内省与剖白
7 H1 w) p$ @1 Q( D& `3 y0 A
6 D# z2 l7 K+ }* t: u《多余的话》,其基调与《可爱的中国》截然相反,是忧郁的、内省的,甚至带有一丝勘破世事的虚无色彩。文章的题目本身就极具味道,充满了自我解构的意味。“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这个开篇,立即将文本定位在一个宏大叙事之外的、极其个人的角落。其风格酷似一篇灵魂的忏悔录,充满了令人心碎的、不加任何伪饰的坦诚。
' A; d# w5 g: ~) l6 d与《可爱的中国》作为一份向外的政治宣言截然不同,这篇文字的核心,是一次彻底向内的、对自我革命身份的无情解构。瞿秋白坦言,他成为领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他深入剖析了自己性格的弱点,认为自己十五年的政治生涯都是在“勉强做着”,像一个“戏子”在扮演着一个他力所不能及的角色。这并非否定革命的理想,而是极其坦白地承认,自己作为一个特定类型的知识分子,在投身这场需要钢铁意志的严酷斗争时,所经历的难以弥合的内心撕裂。他是在用生命的最后时间,来完成一次对自我的“求真”。
% Q5 m- ^5 u" m# P5 G与方志敏那个彻底集体化的“我”不同,瞿秋白在文中的“我”是高度个体化和孤独的。他写作的动机,是“说一说内心的话”,因为他已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这是一种卸下所有社会角色重负后的倾诉,是一次向那个被遮蔽已久的真实自我的艰难回归。他反复强调,不愿“冒充烈士而死”,甚至不希望后来的青年“学我的样子”。他似乎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最诚实、最残酷的文字,将那个扮演着革命领袖角色的公共符号“瞿秋白”,与他内心中那个真实的、矛盾的、软弱的“我”彻底分离开来,以这种方式求得内心的安宁与解脱。 3 t& Z8 S6 Q4 ?5 A$ V
三、 比较与解读
! z" l9 g5 _9 ]6 u4 c k8 [. Q: [6 Z- G) P, |9 D. `# |
3.1 出身、实践与最终心境
: V% Y6 ?" O U5 ^+ Z" `
# |- e8 _5 j! O& X从历史唯物主义那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老话出发,方志敏与瞿秋白最后遗著的巨大差异,几乎是他们各自人生的必然产物,是两条不同生命轨迹的逻辑终点。 ' Z$ o' T# B6 ?8 u. j6 ~
方志敏的意识形态,是他阶级根源和革命实践的直接升华。他的“社会存在”是贫苦的农民出身和扎根于土地的武装斗争。在他那里,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斗争的目标明确而具体——就是为了让和他一样的穷苦人有饭吃、有地种。这种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回到实践的反复循环,锻造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和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精神。《可爱的中国》所展现的集体主义与必胜信心,正是他作为一名从被压迫阶级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真实写照。 % ~& {8 p: Y$ t8 A9 D
瞿秋白的意识则要复杂得多,它尖锐地反映了一个从旧统治阶级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在投身革命后所面临的深刻矛盾。他的“社会存在”是没落的士大夫家庭和主要在书斋、会议室中进行的抽象的、观念性的革命实践。他必须不断用后天习得的理论来改造自己,同时压抑与生俱来的“文人”气质。这种持续的内心斗争,导致了他的理论认知与个人情感在某种程度上的分裂。当外部的政治角色被剥夺,那个被长期压抑的、带有旧阶级文化烙印的个人主义和内省倾向便不可遏制地浮现出来。《多余的话》记录的,也正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迷惘与困惑。
d# U: X$ t9 G9 |" y0 H3.2 理论与实践辩证法的两种不同体现
4 w4 H/ |/ {3 k4 Z$ Y5 l% s7 d, _0 d) c- V+ K/ j3 Z" o
方志敏的革命生涯,完美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praxis)的核心思想——即人通过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活动来认识和确证自身。理论于他,不是需要顶礼膜拜的教条,而是改造现实、解决问题的生动工具。他的意识形态,经过了血与火的反复检验,因而坚不可摧,化为了信仰的磐石。《可爱的中国》所描绘的未来,之所以充满力量,正是因为它已经是他亲手缔造过的现实的放大与升华。 6 R+ {5 [' i+ R2 J3 F
而瞿秋白的悲剧,若简单地将其遗著视为“动摇”乃至“叛变”的证据,未免过于机械和非历史。他的文字,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可能出现深刻矛盾的经典案例。他的悲剧不在于背弃了理论,而在于他未能在个人气质与情感的层面上,完全实现理论所要求的自我改造。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一个人的阶级烙印和早期形成的性格,其“物质”性是何等顽固。 : T! D. j7 m0 o: L) i) h1 u
从某种意义上讲,瞿秋白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参与无产阶级革命时所面临的典型困境。他的思想(上层建筑)真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其内心深处,由旧士大夫家庭背景(旧的物质基础)所塑造的阶级习性依然强大。他的革命生涯,就是一场用先进理论去克服自身落后阶级本能的、极其艰苦的内心斗争。《多余的话》并非反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它是一次极其坦诚的、带有浓厚自我批判精神的唯物主义式剖析,因为它诚实地记录了这份改造之艰难,承认了个人存在的客观复杂性。
# {; ~) M+ M7 u% r结论# ^% o9 b) q4 J0 V' c5 U! y
; O) S# z, E$ B6 L$ [! x, V
所以回到我的主题,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这两份风格上判若云泥的遗著,正是两位革命者迥异的物质生活、阶级背景和革命角色的直接产物。一个植根于农民斗争的火热实践,孕育了献给未来的乐观主义绝唱;另一个则因其士大夫的出身和高层理论家的角色,在长期的内心冲突与挣扎中,留下了充满个人主义色彩和忧郁反思的临终告白。 1 m! D% A' p6 w$ [7 m7 M8 `
当然,作为一个读史的人来说,我们不应、也无法将这两份遗产作简单的优劣之分。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方志敏代表了革命改造客观世界的坚定意志与磅礴力量,是驱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引擎”;瞿秋白则以他无情的自我剖析,代表了革命先锋队,特别是知识分子为实现主观世界的自我改造所付出的巨大精神代价,他的反思是防止革命变得僵化、非人化的重要“警钟”。
9 i- _$ p. I Y! V最终,这两份诞生于失败和死亡前夕的遗著,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中国革命充满辩证张力的、无比真实的立体画卷——既有改造外部世界的宏伟蓝图,也有塑造革命新人的内部挣扎;既张扬而热烈的表达了对未来的无限希望,也沉郁顿挫的包含了个体在历史进程中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与迷惘。他们以截然不同却同样真诚的方式,成为了那个“可爱的中国”最忠实的儿子,单这份在绝境中展现出的不同形态的气节,便值得后人永远的钦佩。
9 g5 ^7 s R& O1 a1 g: ]& |
' A) |: g) N: E! ^# P; x& k- x![]() - Z$ H" I+ M+ y - Z$ H" I+ M+ y
这篇文章是一个很久以前的读书群写读书笔记的时候欠下的文债,当时我就说要好好的对比一下“可爱的中国”和“多余的话”;这次算是理清楚了思路还了旧债吧。
8 v3 O0 E/ A4 b; t
& C/ n/ {/ @! C3 M)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