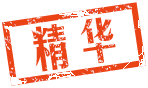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xiejin77 于 2025-7-28 11:50 编辑
# T3 ^/ q& z/ C$ K @, ~# X ]4 W2 f H
第十九章 剥极必复“一派胡言!奇技淫巧!”崔严终于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厉声呵斥,“国朝大事,岂能凭此儿戏之物断定?不过是哗众取宠的妖术!” 他的声音,在此刻却显得如此无力。因为那台机器仍在疯狂运转,那不断上涨的水位,就是最雄辩的证据。 安如谏没有理会他,只是看向魏玄合。魏玄合对他微微颔首。 “陛下,”安如谏转向皇帝,“方才演示的,是‘死局’。接下来,臣将演示‘生路’。” 他走到“乾坤经纬仪”旁,那里早已备好了一个巨大的陶瓮,里面同样装满了水。 “此瓮之水,便是裴侍郎奏章中所提,集中内帑、皇庄,乃至向门阀借贷,所筹措之款项。其名为……加速偿还。” “荒谬!”崔严冷笑,“国库早已空虚,再行借贷,无异于饮鸩止渴!” 安如谏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魏玄合。 魏玄合缓步走出,站到那台仍在咆哮的机器前。他的目光扫过那即将溢出的“债务”之池,扫过那两个盛满“恐惧”与“怨恨”的副池,扫过那疯狂转动的魔鬼水轮。 “陛下,请看,”他指着眼前的景象,声音沉静而有力,“《周易》有卦,名曰‘剥’。山附于地,阴盛阳衰,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长。此刻我大唐之局,便是这‘剥’卦之象,阴气已至五爻,阳气仅存一脉,摇摇欲坠,国之根基,即将被侵蚀殆尽。” 他的话,让所有人都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剥极,则将无所复。此时此刻,任何常规的、零敲碎打的‘还款’,都如杯水车薪,只会成为助长阴火的薪柴。”魏玄合话锋一转,眼中爆发出惊人的光芒,“然,《易》之道,在于变!剥之终,则为复!当阴气盛到极致,阳气必将自绝处而生!” 他猛地一挥手:“安先生,动手!” 安如谏不再犹豫。他与助手合力抬起那只巨大的陶瓮,没有丝毫迟疑,将其中所有的清水,如同一道白色的瀑布,一次性地、猛烈地,全部倾泻进了那个代表“债务”的琉璃池中! “轰——” 水声轰鸣,震惊百官。 奇迹发生了! 那股强大的、集中的水流,如天河倒灌,瞬间将“债务”池的水位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顶峰!那只代表“利滚利”的魔鬼水轮,在这股沛然莫御的力量冲击下,先是猛地一滞,随即发出一声哀鸣,竟被强行反向冲刷,彻底停摆! 紧接着,被瞬间充满的“债务”池,其水位远远超过了那两个流向“恐惧”与“怨恨”的溢流口,而是从一个更高处、专为“清偿”而设的巨大排水口,奔涌而出,流向了机座之外! 前后不过数息之间,那咆哮的机器,安静了。 曾经沸腾的“债务”之池,水位急剧下降,恢复了平静。两个代表“恐惧”与“怨恨”的副池,再无水源注入,其中的存水,也顺着底部的管道,缓缓流走,象征着人心安定,秩序恢复。 整个系统,被强行逆转! “此,即为‘复’!”魏玄合的声音,如洪钟大吕,在寂静的大殿中回荡。 “一阳来复,于寂灭之处,重开生天!这并非简单的‘还债’,而是以雷霆万钧之‘阳’,破除那盘根错节之‘阴’!是洞悉系统‘势’之流转,于最关键之节点,行非常之举,强行扭转乾坤!陛下,此非‘术’,此乃顺天应人、剥极必复之‘道’!” 道与术,在这一刻,于这座帝国的最高殿堂之上,于一场惊心动魄的视觉奇观之中,完美地融为一体。
0 q7 A1 I" _4 _
% y" z3 N$ M! c- \4 `' _1 Y1 X7 C第二十章 天子之断皇帝李哲,怔怔地站在那里。 他的身体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一种混杂着后怕、震撼与狂喜的激动。 他的一生,都在学习如何平衡。平衡朝堂,平衡人心,平衡国库的收支。他早已习惯了妥协、折中与循序渐进。 而今日,这三个在他看来早已走投无路的人,却为他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可能:一种属于帝王的、大开大合的、以雷霆之势扭转乾坤的可能。 安如谏的“术”,让他清晰地看到了危机的骨骼与脉络,那是一种冰冷、严酷、不容置疑的理性。 魏玄合的“道”,则为这冰冷的理性,注入了宏大、磅礴、充满东方智慧的灵魂。 原来,挽救危局,靠的不是小心翼翼的修补,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与智慧! 他缓缓地坐回龙椅,目光第一次从那台神奇的机器上移开,落在了崔严的身上。那目光,不再有丝毫的犹豫和困惑,只剩下冰冷的、属于君王的审视。 “崔严。” 皇帝的声音很轻,却让崔严浑身一颤,如坠冰窟。 “你明知‘子母相生’之法的酷烈,却力主将其写入契约。” “你明知清淤工程陷入泥潭,却百般阻挠任何补救之法,坐视债务疯长。” “你明知国库将倾,社稷动摇,却在此刻,力主斩杀唯一能看懂问题之人,意图死无对证。” 皇帝每说一句,便向前探一分身子,龙袍上的金线在烛火下闪着森然的光。 “你并非不知这债务是头恶兽,你只是想等它长得足够大,大到可以吞噬掉你的政敌,大到只有你崔氏一族能站出来‘收拾残局’,届时,你便可挟恩图报,名利双收,将这大唐的财权,尽数纳入你门阀之手!” “朕说得,对也不对?” 最后一句,已是雷霆之问。 崔严面如死灰,双腿一软,瘫倒在地。“陛下……臣,臣冤枉……” “够了。”皇帝挥了挥手,脸上满是厌恶与疲惫,“将崔严及其党羽,拿下!交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司会审!朕要看看,这盛世之下,究竟还藏着多少此等蛀国之贼!” 如狼似虎的金吾卫一拥而上,拖走了早已失魂落魄的崔严。一场持续了数月的、席卷了整个朝堂的惊天危局,在这一刻,以一种谁也未曾想到的方式,落下了帷幕。 皇帝的目光,最后落在了殿中的三人身上。 那个曾经被他斥为“误国之贼”的年轻侍郎,此刻正静静地看着他,眼神中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只有一种对真理的执着。 那个曾经因“失察”而信仰崩塌的白发老者,此刻却目光澄澈,仿佛重获新生。 还有一个碧色眼眸的异乡人,他抱着那台奇特的“乾坤经纬仪”,像抱着自己的孩子。 “裴渡,”皇帝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感慨,“朕……错怪你了。官复原职,清淤之事,朕命你全权主持。所需款项,依‘加速偿还’之法,内库……全力支持!” “魏玄合,”他看向老监正,“你为大唐,找到了‘道’与‘术’的钥匙。朕封你为‘文贞先生’,入崇文馆,为太子师。”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安如谏身上,这个让他又惊又奇的波斯人。 “安如谏,”皇帝沉吟片刻,缓缓说道,“你的学问,朕看不懂,但朕看到了它的力量。朕敕令,于国子监内,增设‘算学馆’,由你执掌。朕给你钱、给你人,朕只有一个要求:将你的学问,传于大唐。朕要让后世子孙,既懂我中土之‘道’,亦明你西来之‘术’。” 一道道敕令,如春雷滚过,宣告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紫宸殿外,晨曦初露,金色的阳光刺破云层,为这座古老的都城,镀上了一层温暖而明亮的光辉。 裴渡、魏玄合、安如谏,三人并肩立于殿前白玉阶上。他们一个身在尘世,一个心在天外,一个来自远方,却因一场共同的危机,命运交汇,最终锻造出了足以扭转乾坤的合力。 他们望着远方升起的朝阳,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但他们的心中,已再无畏惧。因为他们知道,当智慧与勇气相遇,当“道”与“术”同行,这世间,便没有解不开的危局。 尾声
: q& \8 ?. V3 i9 A! T% `
# q) K7 j1 f0 y/ Y4 E
神龙新岁,神都洛阳城在一场瑞雪之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与生机。天元危局,那场几乎将帝国拖入深渊的风暴,已然过去整整一年。曾经飞涨的米价早已平稳,漕运往来不绝,市井间的喧嚣再次充满了饱暖之后的闲适与活力,仿佛那段人心惶惶的日子,只是一场被飞雪掩埋的噩梦。 然而,有些东西,却被这场风暴永久地改变了。 户部衙署内,新任的户部尚书裴渡,正伏于案前。他的官袍换了颜色,位阶已是百官之首,但眉宇间那股凌人的锐气却收敛了许多,代之以一种久经砥砺的温润与沉稳。他的桌案上,不再仅仅是堆积如山的账目与赤字惊人的卷宗,更多的是来自各州府关于民生、仓储、乃至民心向背的详细奏报。 他手边摊开的,并非官样文书,而是一部他亲手编撰的书稿。书页上,既有安如谏那些精妙绝伦的代数符号,也有魏玄合那充满玄思的卦象图谱。一行行清隽的小楷,将二者巧妙地联结、诠释。他为这部心血之作取名为——《乾坤经纬新论》。 “……国之财政,非冷铁之数,乃生民之血脉。其流转增减,上应天时,下系人心。故善为政者,不惟算其‘量’,更当察其‘势’。势者,民心之向背,官心之安危,万物消长之机也。术可尽其流,道能溯其源。以西来之精密算学为纬,以中土之易理哲学为经,经纬交织,方可一窥天下大势,曲成万物而不遗……” 他搁下笔,目光投向窗外。他仿佛看见了那台在金殿之上逆转乾坤的“乾坤经纬仪”,那流动的算式,不仅洗刷了他的罪名,更洗练了他的灵魂。他终于明白,数字的尽头,是人心。而经世济民的真正要义,是于冰冷的算式中,找到那一点属于人的温度。 , c! m9 N3 t' c% W) G4 g
3 |; c7 W( a! \4 D1 n. @$ r! M在神都洛阳城南,一处由皇家赐建的院落,已经成为整个神都最引人瞩目的所在。高大的门楣上,悬挂着御笔亲题的匾额——格物致知院。 这里没有国子监的森严礼法,也没有崇文馆的皓首穷经。院中,一群肤色各异、衣着不同的年轻人,正围着一个巨大的沙盘激烈地争论着。他们时而用汉话引述《周易》的爻辞,时而又在一方黑色的石板上,用白石笔画出安如谏教授的代数方程,试图模拟一场蝗灾对来年粮价的动态影响。 廊下,魏玄合与安如谏正并肩而立,含笑看着这番景象。 魏玄合须发皆白,精神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矍铄。他不再是那个执着于窥探天命的司天监,而是一位真正的大宗师。他为学生们讲解《易》理,却不再拘泥于吉凶卜算,而是引导他们去理解卦象背后那套关于系统、变化与平衡的宏大世界观。 安如谏则换上了一身唐人常穿的圆领袍,碧色的眼眸里,再无昔日的孤独与警惕,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找到归宿的安然。他终于可以让他的代数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与最深邃的智慧相结合,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他的学问,不再是屠龙之技,而是能被这些聪慧的年轻人所理解、所应用的济世之学。 东西方的智慧,在这座小小的院落里,以前所未闻的方式,开始了真正的融合与生长。 / d" P O3 g+ N% |! N3 S
, v: X+ U* L$ I4 M2 K2 c+ D
夕阳西下,将天边的云霞染成一片绚烂的赤金。 魏玄合与安如谏走出格物院,并肩散步于山下的一条小径上。暮色中的神都洛阳城,轮廓分明,万家灯火渐次亮起,如繁星落于大地,宁静而温暖。 “玄合先生,”安如谏望着远方的景致,用已十分流利的汉话感慨道,“一年前,我以为我的数学,可以计算世间万物。但现在我才知道,我能算出的,只是万物的影子。” 魏玄合微微一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而我,穷尽一生,试图抓住那影子的主人——‘道’。却险些被‘道’的虚无所吞噬。直到遇见你,我才明白,若无影,我又如何知晓光的存在?” 两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他们走过一片水塘,晚风吹皱了池水,将落日的余晖与岸边的树影揉碎成一片流动的光斑,变幻不定,无法描摹。 安如谏停下脚步,长久地凝视着那片涟漪,轻声说道:“我们的‘乾坤经纬仪’,可以模拟国库的消长,可以推演人心的向背。但它永远也算不出,下一阵风,会从何处吹来,又会将这池水,吹拂成何种模样。” 魏玄合负手而立,苍老的眼眸中,映着天光水色,透出一种大彻大悟后的澄明。他缓缓点头,发出一声悠长而深刻的感慨: “是啊,天元可测,人心难算。” 这声音,没有丝毫的无奈与气馁,反而充满了对世界复杂性的敬畏,与对求知问道永无止境的释然。 一年前,他们以为自己能算尽天下。一年后,他们方知人力终有穷尽。而这,或许才是他们从那场天元危局中,学到的、最宝贵的智慧。 远方,神都的灯火愈发璀璨,如同一片永不熄灭的星海,静静地见证着过往,也温柔地照亮着未来。
* z- P( Q: B7 n 全文完 ' T2 x; U1 M! t
$ ]& l% @9 n& ?) K
' ^; W: R7 Y: N/ k" B$ G% B; n,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