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吱声
标题: 神都烟火志之点绛唇 [打印本页]
作者: xiejin77 时间: 2025-8-6 21:41
标题: 神都烟火志之点绛唇
本帖最后由 xiejin77 于 2025-8-7 18:51 编辑
$ y2 G5 z2 Z( d0 @/ R: `* G' O6 O7 G/ q, Q4 E- @
术数志已经是两篇了,烟火志也不能只有一篇,半两食铺之外,神都的烟火如斯绽放……
# T" @/ [* U+ u' l0 v, `0 y! e2 C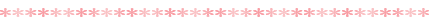 5 a! n7 U0 n: K
5 a! n7 U0 n: K
" `' F! Y( S* \- L. e神都烟火志之点绛唇- |0 c! Z8 M( p% Y6 Y1 u
( v# M% @0 o$ d! v$ v& P壹0 x2 r2 q, S) m2 i
2 J3 v7 n- Q3 o2 J: E5 f
8 q& \" g8 d( @# F# i
# k& v9 U1 X. \/ A7 w s阿萦觉得,龙门山的石头是有气味的。
这气味不属于山上终年缭绕的香火。那气味太过郑重,是无数信众将沉甸甸的祈愿与希冀,揉碎了、点燃了,化作的一缕缕青烟,闻久了,心会跟着变得不轻省。这气味也不属于络绎不绝的香客游人带来的人间气。那气味是浮动的,混杂着汗、衣料、脂粉与各色香料,像一阵忽然而至的热风,喧闹是喧闹,吹过了无痕,反倒衬得山更空寂。
石头的气味,是它自己的。是亘古的、沉默的、不与人言说的。
清晨,天还未亮透,是一日之中山最静的时刻。伊水上的雾气便浩浩荡荡地漫上山腰,无声无息,像一大块浸透了清寒的生宣,将山峦树木都洇染成深浅不一的墨色。石头在这雾里,便像一块刚从深井里捞出来的冬瓜,触手生凉,带着一股子最原始的、未曾被人间烟火侵扰的生涩。阿萦卯时起身,提着空木桶去涧边汲水,赤足走在冰凉的石阶上,脚步声在寂静的山谷里显得格外清晰,空,空,空,像时间在叩问,又像一颗孤独的心跳。她呼出的白气和山间的雾融在一起,那一刻,她觉得自己也快变成了一块吸饱了水汽、内里却冰冷的石头。
到了晌午,尤其在夏秋之交,日头便毒辣起来。阳光没有丝毫遮拦地泼洒下来,山道上蒸腾起白花花的热浪,看久了,眼睛都会被晃得发花。石头被晒得滚烫,你若是不小心用手背碰一下,能激得人一哆嗦,像是碰到了烧红的烙铁。这时候,石头的气味就变了。那是一种极其干燥、极其古老的气息,仿佛把千百年来吸收的每一缕日光,都在此刻浓缩、蒸馏,再用一种极其缓慢、极其固执的方式,缓缓地释放出来。那气味有点像药铺里陈年的药材,又有点像被反复翻晒过的旧书卷,沉郁,安静,带着一股子让人不得不肃穆下来的力量。阿萦常常坐在师父为她搭的脚手架上,背对着烈日,给佛像描摹衣纹,汗水顺着发际线往下淌,淌到脖颈,痒痒的,像小虫在爬。她闻着那股子味道,人会不自觉地变得安静,心里那些浮躁的、杂乱的念头,也像是被这烈日下的老石给镇住了,一点点沉下去,沉到一个很深、很静的地方。
她在这儿,已经待了五年。
五年前的洛阳城,刚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饥荒。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据说能埋住半截坊墙。她还不叫阿萦,没有名字,只是南市饥民里一个面黄肌瘦、头发枯黄得像一团乱草的丫头,每天想的,就是如何从别人指缝里多抠出一点吃食,好让自己活过明天。那天,她正为了半块发了霉的干馍,和一個比她高半个头的半大小子打得头破血流。那馍是她从一条野狗嘴里抢来的,上面还带着狗的唾沫。她把那小子咬了,自己也被抓得满脸花。她死死地护着那块馍,那是她三天的口粮,是命。就在那时,一双纤尘不染的皂靴停在了她的面前。
她抬起头,逆着灰白色的天光,看见一个穿着青色官服的中年人。那人身形清瘦,留着三绺打理得极其整齐的胡须,眉头微微皱着,眼神却很亮,像两颗浸在清水里的黑石子。他没有看她的脸,也没有看她怀里那块脏污的馍,他的目光,直直地落在了她那双紧紧攥着干馍、指甲缝里全是泥污的手上。那是一双瘦得只剩下骨头的手,青筋毕露,却异常的稳。
“你这双手,”他说,声音不高,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像工匠用锤子敲在石头上,清脆,坚实,“天生是握笔的。”
她那时哪里懂得什么是握笔,她只觉得这人身上的皂角味真好闻,干净,清爽,像雨后山里的青草,是她从未闻过的味道。她也看见,这人身后的随从,手里提着一个描金的食盒。她盯着那食盒,狠狠地咽了口唾沫,喉咙里发出咕咚一声响。
这人,便是她后来的师父,将作监从九品画官,王道玄。
师父专管皇家在龙门山督造佛窟的“点绛唇”一事。所谓“点绛唇”,就是在雕凿好的佛像上敷彩、开光。师父说,这不是画画,这是修行。给佛妆金身,是一桩能泽被子孙的天大功德。因此,手要净,心更要净。心里但凡有一丝杂念,笔下的佛,就睁不开眼,渡不了人。
阿萦每天都在“修行”。她的工作,是研磨颜料。这活计看似简单,却是“点绛唇”工序里最基础,也最考验心性的一环。她调的颜料,是天下最好的。石青、石绿,得上好的阿富汗青金石、波斯孔雀石,先用铁杵捣成粗砂,再用最细的绢筛筛去杂质,然后加进按秘方熬好的鹿角胶,倒进一只厚重的石钵里,拿着光滑的石杵,一遍,一遍,又一遍地细细研磨。
这活计,急不得,也缓不得。快了,胶会发热,颜色就“死”了,失去温润的光泽。慢了,胶会凝固,颜料便不匀,画出来的色彩会有滞涩感。你得用一种恒定的、不疾不徐的力道,手腕带动着石杵,在石钵里画着一个又一个圆。日复一日,从日出到日落,胳膊酸得像是要断掉,腰也直不起来。有时候磨得久了,她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不是在磨颜料,而是在磨时间,磨自己。把那些属于山下饥民的、野狗一样的记忆,连同那些坚硬的矿石,一同磨成最细腻的粉末。
可当你把最后磨好的颜料倒出来,看着它们在蚌壳里呈现出那种如膏脂般细腻、如宝石般温润的光泽时,心里又会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用这样的颜料点染出来的菩萨,衣袂能临风飘动,眼神能含波流水。
这天,她正在修补的是宾阳中洞的一尊胁侍菩萨。这尊菩萨的面相最是慈悲,嘴角微微上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悲悯又温柔。可历经百十年风雨,伊水湿气的侵蚀,那点笑意有些斑驳了。嘴角的朱砂淡了,像说了太多无声的法,有些疲惫。脸颊上的金色也脱落了几处,露出底下青灰色的石胎,平添了几分沧桑。师父让她来补,说她的心最细,手最稳,整个画坊的弟子里,只有她,能还原这尊菩萨最初的神韵。
阿萦坐在一个半人高的木制脚手架上,这是她自己搭的,用卯榫结构,结实,稳当,没有用一根钉子。她左手手腕上挂着一个小小的竹篮,篮里放着几只充作调色盘的蚌壳。蚌壳里是朱砂、赭石、藤黄,还有用鱼鳔胶新调的金粉。山风顺着洞口灌进来,凉飕飕的,吹得她额前的碎发轻轻飘动,也吹得篮边一盏防风油灯的火苗,一下一下地晃,将她的影子,和菩萨的影子,投在石壁上,交叠在一起。
她屏住呼吸,右手悬腕,用一支师父赏的“叶筋笔”——笔锋是用上好的黄鼠狼尾尖的毛做的,细韧有弹性,宜画线条——蘸了饱满的朱砂,朝那菩萨的嘴唇,极慢、极稳地,点了下去。
这一笔,叫“点绛唇”。是为佛像开脸的最后一笔,也是最关键的一笔。这一笔下去,佛,就活了。
她离佛很近,近得能数清他脸上石质细微的纹理,能看见他眼角那一粒不知停留了多少年的尘埃。她甚至能想象出百年前那位无名石匠,是如何一锤一锤,将这份慈悲从坚硬的石头里,解放出来。他或许也曾像她一样,为了一顿饱饭而挣扎过吧?
可她又觉得,佛离她很远。
她看着这尊含笑的菩萨,心里想的,却是山下那个热闹的集市。
那个集市有个雅号,叫“静心斋”,可卖的东西,却没一样能让人静心。阿萦想的是集市口那家“半两食铺龙门店”。铺子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大叔,叫老王,永远一副笑呵呵的模样,肚子挺得像尊弥勒佛。他家的羊肉汤是一绝。用大骨熬足了四个时辰,汤色奶白,浓而不腻。点一碗汤,老板会麻利地切上几片烫得恰到好处的薄羊肉,再抓上一大把碧绿的芫荽,末了,再淋上一小勺自家炼的羊油辣子。那香味,霸道,直接,能顺着风飘出半里地,勾得人心里的馋虫直打滚。
若能就着这么一碗滚烫的羊肉汤,再来一个刚出炉的胡饼……
她想起那胡饼。是隔壁张二哥的摊子卖的。那胡饼,用的是最古老的吊炉,炉膛深,火力猛。贴进去的饼,一面烤得焦黄酥脆,另一面却依旧柔软。饼上洒满了脱了壳的白芝麻,烤得香气四溢。趁热掰开,一股麦香混着葱油的香气,直往鼻孔里钻。用那饼,蘸着羊肉汤吃,那滋味……
阿萦手里的笔,极轻微地,颤了一下。
——坏了。
她心里咯噔一声,赶紧收回笔。定睛看去,菩萨嘴角的笑意,似乎僵硬了一瞬。那点刚刚补上去的朱砂,好像也比旁边的旧色,深了那么一星半点,像一滴凝固的血。
她赶紧收回笔,在蚌壳里重新润了润。心里一遍遍地念叨:佛祖莫怪,弟子不是故意的,弟子再也不敢了。
可她知道,这不是第一次了。
她给奉先寺那尊卢舍那大佛的面颊敷金时,满脑子想的,都是上元节时洛阳城里的灯。天津桥上,火树银花,龙灯、凤灯、走马灯、兔子灯……满城流光溢彩,像天上的银河落到了人间。那光,比她手上调和的金粉,要亮得多,也暖得多。金粉是冷的,是属于佛的;灯火是暖的,是属于人的。
她给潜溪寺那些金刚力士的臂膀描绘肌肉线条时,她想的,是伊水边上那些光着膀子拉船的纤夫。他们的脊背被毒日头晒成油亮的古铜色,肌肉像石头一样一块块坟起。汗水顺着肌肉的沟壑往下淌,在阳光下闪着光。纤绳深深地勒进他们的肩胛,每一步都踏在湿滑的泥泞里,口中喊着苍凉而有力的号子。那才是真正的力量,是与天争、与水斗的、活生生的力量。比起这些,石窟里这些摆着固定姿势的力士,未免太干净,也太寂寞了。
师父说她,“身在佛国,心无敬畏”。这话,说对了一半。她不是没有敬畏。她敬畏每一块石头,敬畏每一位将毕生心血凿进这石壁的无名匠人。她只是……更惦记那些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佛国太静了,太干净了,连风都是寂寞的。而人间,哪怕是吵闹的,脏污的,都有一种让人心里踏实的暖意。那种暖意,是实实在在的,能吃进肚子里,能穿在身上,能听在耳朵里。
她有一个秘密。
在她床铺底下的一只小木箱里,锁着一卷素绫。那素绫,她轻易不示人,连最要好的师姐妹都没见过。那上面,没有一尊佛,没有一朵莲花,没有一片象征祥瑞的云彩。
她画的是她五年来,每一次下山采买物料时,偷眼看来的市井百态。
有当垆卖酒的妇人,丰满的胳膊搭在酒瓮上,眼神懒洋洋的,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像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戏。有街角斗鸡的闲汉,为了几个铜板,争得面红耳赤,输了钱的那个,气得脖子都粗了。有捏糖人的老汉,吹一口气,一个半透明的孙猴子便活灵活现地成了型。还有坐在“半两食铺龙门店”门口,埋头呼噜呼噜喝羊肉汤的脚夫,他的草鞋沾满了泥,额上的汗珠,混着汤的热气,一颗颗往下掉。
她给这幅长卷起了个名字,叫《神都烟火图》。
只是这幅图,还缺了许多颜色。画人容易,画出那股子活色生香的“气”来,难。她总觉得,自己画出的人物,皮肤、衣衫,都少了一种被日光、风尘和岁月浸润过的质感。那是一种温暖的、厚重的、带着生命光泽的颜色。
她需要一种特殊的颜料。
那颜料来自一种矿石,叫“晕金石”。师父的藏珍阁里,有那么一小块,是早年西域进贡的。石质是沉郁的赭红色,像黄昏时分的火烧云,又像凝固的牛血。但在那一片沉静的赭色深处,又蕴藏着无数点点碎金。日光下看,那些金点会像活了一样,在赭色里流转游走,变幻出迷离的光晕。
师父说,此石有灵,非画神佛不可用。用它磨成粉,调出来的颜色,既有泥土的厚重,又有黄金的华彩。用来画菩萨的肌肤,或是佛陀背后那圈最神圣的头光,最是传神。
可阿萦想的,却是用它来画夕阳下里坊的瓦片,画烤胡饼时那焦黄的表皮,画那个拉船纤夫古铜色的脊背。她觉得,那种颜色,才是晕金石真正的归宿。
师父库房里那块,是御赐之物,她想都不敢想。她只能自己去寻。
她曾托下山采买的师兄打听过。整个龙门山下的集市,乃至洛阳城里,卖这种稀罕矿石的,只有一家。就在“静心斋”集市的尽头,一棵大槐树底下。铺子没有正经的门脸,主人是个叫小乙的年轻人。
补好了菩萨的唇,她仔仔细细地收拾好工具。天色已近黄昏。夕阳的余晖从洞口斜斜地照进来,给佛像们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光。它们依旧沉默着,用千百年不变的姿态,俯瞰着洞外那片慢慢被暮色笼罩的红尘。
阿萦背起沉甸甸的画具箱,走出石窟。山风迎面吹来,带着草木的清香和伊水的水气。她深吸一口气,觉得胸中的烦闷,消散了不少。
脚步,也轻快了许多。
明天,她要告一天假。
下山去。
去那个吵闹的、不安静的“静心斋”,去寻找她的“晕金石”,也去寻找她画卷里,欠缺的那一抹人间真色。
, f8 K3 a! I; \( b6 Q
7 t4 c, P- c2 @9 O; z
作者: xiejin77 时间: 2025-8-8 09:00
贰4 E7 H& |+ T T$ E3 |7 A7 z: W
, x/ X3 A9 ^2 h1 m% K$ V# d9 q
龙门山下的集市,沿着伊水岸边的驿道自然生发出来,蜿蜒一两里地。南来北往的客商,上山拜佛的香客,附近村镇的百姓,还有山上那些画工石匠的家眷们,都汇集到这里。这地方有个附庸风雅的名字,叫“静心斋”,也不知是哪个手头阔绰的读书人,在此处修了個別业,随口起的。可这地方,却是神都左近最不“静心”的所在。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伊水的水面上起,这里就活了过来。它像一锅被点燃了灶火的粥,咕嘟咕嘟地,先是冒起细小的泡,然后便彻底沸腾了。
讨价还价声、吆喝叫卖声、驴子骡子的嘶鸣声、孩童的哭闹追逐声、还有那走街串巷的货郎摇动的拨浪鼓声,混成一片,热闹得能把人的耳朵震麻。空气里,也充斥着各种复杂而顽固的气味:伊水带来的潮湿水汽,鲜鱼的腥气,牲口的粪便味,女人们身上廉价的脂粉香,男人们身上的汗味,还有从各色食铺里飘出来的、最最诱人的食物的香气。
阿萦不常来。她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又是在山上清修的,师父管得严,不许她们随意到这龙蛇混杂之地闲逛。偶尔下山采买,也是来去匆匆,恨不得能贴着墙根走,避开所有人的目光。她嫌这里太吵,人味儿太重,那股子生猛的、毫不掩饰的活泛劲儿,让她这个在清静佛地待惯了的人,有些无所适从,像一只误入闹市的鹿。
可今天,她却一头扎进了这锅滚开的粥里。
她换下那身沾满颜料的青布工装,穿了一件半旧的月白色襦裙,外面罩了件浅碧色的短衫。这是她除了过年,最好的一身体面衣裳了。头发也仔细梳过,用一根素银簪子绾了个简单的发髻。她依旧低着头,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寻常来赶集的邻家女儿,可那双因常年握笔而显得格外稳静的手,和那周身洗不掉的、淡淡的墨香与松烟气,还是让她与周遭的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她沿着河岸的石板路,顺着人流往前走。
一个卖糖葫芦的老汉从她身边走过,那裹着晶亮糖稀的山里红,在阳光下像一串红玛瑙,看得人腮帮子发酸。阿萦咽了口唾沫,加快了脚步。
她路过了“半两食铺龙门店”。铺子不大,就是三间茅草屋连在一起,门前用几根木头搭了个棚子,棚下摆着四五张粗糙的矮脚木桌和长凳。此刻,桌边坐满了人。有刚从伊水码头上来的船工,光着膀子,露出油亮的黑皮肤,正端着一只大陶碗,吃得满头大汗。有几个看起来像附近庄子上的农人,就着一碟咸菜,在喝着劣质的米酒。还有两个穿着体面的管家模样的人,大概是山上哪位贵人府上的,正低声交谈着什么。
铺子老板老王,那个胖大叔,正乐呵呵地在炉灶和桌子间穿梭,他的围裙油光锃亮,嗓门洪亮:“来喽!您二位的羊杂汤!”他把两碗热气腾腾的汤“哐”地放在桌上,汤汁都溅出来少许,“慢用!”
一股浓郁的、夹杂着羊肉、胡椒和芫荽的香气,霸道地钻进了阿萦的鼻子里。她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咕”地叫了一声。她脸上一热,脚下走得更快了,几乎是逃一般地离开了那股香气的笼罩范围。
她要找的铺子,就在这“静心斋”集市的尽头,远离了最喧闹的地段。那里有一棵巨大而苍老的槐树,树冠如盖,投下一大片浓密的荫凉,像一把撑开的巨伞,为树下的一切遮蔽着烈日。
铺子就开在槐树底下。没有招牌,没有门脸,也是三间茅草屋,前面搭了个棚子,棚子下、屋檐前,乱七八糟地摆满了各色货物。有大块的、未曾雕琢的青石、花岗岩;有一捆捆大小不一的木料,散发着松木、柏木、檀木等不同的气味;还有许多装在箩筐和麻袋里的零碎,看起来像是各色的矿石、贝壳、甚至是晒干的怪异植物。
这就是小乙的铺子。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铺子。
人们都叫他小乙,没人知道他的大名,也没人知道他的来历。听说他是三年前从关外流落到神都的,也不知使了什么门道,竟盘下了这块集市尽头的地。他卖的东西极杂,主要是给山上那群画工、石匠们提供些材料。从最普通不过的石料、木材,到研磨颜料用的矿石,再到一些稀奇古怪、用作雕刻的树根和奇石。生意看起来不大,做的都是些零散买卖,但奇怪的是,听说连洛阳城里那些赫赫有名的大画斋、大行会的管事,有时候也会派人来他这里,寻些市面上难得一见的稀罕物。
阿萦远远地站在那棵大槐树的荫凉里,心里有些打鼓。
铺子前正围着几个人。一个看起来像是某个大户人家的管家,四十来岁,衣着光鲜,正指着一块半人高的青灰色石头,唾沫横飞地说着什么,似乎是在拼命地往下砍价。
而小乙,就蹲在那块石头旁边。
他背对着阿萦,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旧的深蓝色土布短衫,袖子高高挽起,露出两截在日光下泛着健康光泽的、结实的小臂。他似乎完全没有听那管家在说什么,只是专心致志地,拿着一块湿布,一遍遍地擦拭着那块其貌不扬的石头。
他擦得很慢,很仔细,仿佛那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是什么稀世珍宝。他会顺着石头天然的纹理擦,遇到凹陷处,还会用手指包着湿布,探进去,把里面积攒的尘土一点点抠出来。
阳光透过槐树叶细密的缝隙,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的头发很黑,用一根灰色的布条随意地束在脑后,有几缕不听话的发丝垂在脖颈上,随着他的动作,轻轻地晃动。
阿萦看着他的背影,不知为何,脑海里忽然浮现出自己曾经临摹过的一尊年轻罗汉的壁画。那尊罗汉也是这样,微微弓着背,神情专注地在修补自己脚上的一双草鞋,对周遭的一切都浑然不觉。那是一种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近乎于虔诚的安静。
那管家还在喋喋不休,从这石头的成色,说到市场的行情,引经据典,说得口干舌燥。小乙却置若罔闻。他把石头的每一个角落都擦拭干净了,然后站起身,退后两步,像个画师审视自己的作品一样,眯着眼打量了片刻。接着,他走上前,伸出手指,在石头上几个不同的地方,轻轻地敲了敲。
“叩,叩叩。”
声音清脆,竟带着些微不同的回响。他侧着耳朵,专注地听着那声音,嘴角甚至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
做完这一切,他才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过身来。
阿萦也终于看清了他的脸。
那是一张很年轻的脸,大概也就二十岁出头的样子。五官算不上多么英俊,却很生动,让人看一眼就能记住。皮肤是常年在户外劳作晒出的麦色,健康,紧致。眉毛很浓,像两把刷子,斜斜地飞入鬓角。眼睛不大,是那种狭长的丹凤眼,眼尾微微上挑,但眼珠却黑得惊人,像两颗刚刚被山泉水洗过的、浸在水里的黑石子,亮得摄人。
他一笑,嘴角就用力地向上咧开,露出一口整齐的、雪白的牙齿。那笑容里,透着一股子少年人特有的、混合着机灵和狡黠的爽利劲儿。
“钱管家,”他开口了,声音清朗,像山涧里流淌的泉水,撞在石头上发出的声音,“您瞧,这块‘太湖响石’,妙就妙在这儿。”
他伸出手指,在石头表面一道天然形成的、蜿蜒的白色水线上划过:“您看这条线,像不像咱们伊水十八弯?从龙门山脚,一路绕到偃师。您再听这声儿,”他用指节又敲了一下,石头发出一阵“空……空……”的回响,清越悠扬,仿佛能传出很远。
“这叫‘空谷足音’。这石头,肚子里是空的,心是实的。您把它请回去,摆在您家老太爷的书房里,不比那些俗气的玉器瓷器,更有味道?老太爷写字累了,敲上一敲,听听这山谷里的声音,岂不雅哉?”
那钱管家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本来一脸的精明,此刻却也露出了几分迷糊。他凑过去,仔细看了半天那道水线,又学着小乙的样子敲了敲,听了听声音,果然觉得这块灰不溜秋的石头,好像越看越不一般了。
小乙见状,嘴角的笑意更浓了:“您是行家,我小乙也不敢蒙您。这石头,是我一个月前,亲自从嵩山深涧里,和两个伙计一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背出来的。就这么一块,错过了,您再上哪儿找去?您要是诚心要,这个数。”他不动声色地伸出三根手指。
钱管家皱了皱眉,似乎嫌贵,犹豫起来。
小乙立刻把手收了回来,脸上的笑容也淡了些,甚至带上了一点遗憾和不舍:“那就算了。这石头跟我有缘,说实话,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卖。您再上别处看看?兴许城里东西两市,能有比这更好的。”
他说着,转身就要把那块半人高的石头往屋里搬。他看着不甚健壮,但一俯身,双臂一用力,那石头竟被他硬生生地抱离了地面。
“哎,哎,小乙哥,别急啊!”那钱管家一看他来真的,赶紧上前拉住他,“三贯就三贯!我这就给您取钱!”
一桩看起来快要谈崩的生意,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做成了。
阿萦在槐树的荫凉里,从头到尾,看得分明。她虽然不懂奇石,但也隐约觉得,那不过是一块略有些奇特的青石罢了。所谓的“伊水十八弯”,不过是天然的一道裂纹;那“空谷足音”,或许也只是石头内部恰好有些孔洞。可被小乙这么天花乱坠地一说,死的都变成了活的,还平添了几分文人雅趣。她心里暗暗佩服,这个年轻人,真是个天生做生意的料。那张嘴,怕是能把稻草说成金条。
等那钱管家喜滋滋地唤了两个仆役来,把石头抬走,铺子前才算清静下来。
小乙拿着钱管家给的几串沉甸甸的铜钱,在手里掂了掂,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他一抬眼,便看见了不远处,站在槐树下,一直望着这里的阿萦。
他似乎愣了一下。那双黑亮的眼睛,在她身上不着痕迹地打量了片刻。从她干净却半旧的衣衫,到她那双略显局促地交握在一起的手,最后,落在了她那张略显苍白、神情有些紧张的脸上。
阿萦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下意识地拢了拢衣襟,心跳得有些快。
“姑娘,”小乙问道,脸上又挂上了那种随和又带点精明的笑容,“要点什么?买石头,还是买木头?”
阿萦定了定神,从树荫下走了出来,走到铺子前。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些,不带波澜。
“店家,你这里……”她顿了顿,深吸一口气,才问出那个让她心心念念的名字:“可有‘晕金石’?”
) V8 s/ A3 `# n# u. z
$ ], S/ J9 r6 H
% k8 K8 B k3 O* h# ?
作者: xiejin77 时间: 2025-8-8 19:05
叁 d$ e0 ] n) r
4 d$ S4 j; Y2 q( b, P% B
4 x' ^( k9 u. v0 B' h! g8 A V
& ]* ]& C5 E# J听到“晕金石”三个字,小乙脸上的笑容,有了一丝微不可察的变化。他那双黑亮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像一只正在打盹、却突然听见猎物动静的猫。那种慵懒随意的神情瞬间褪去,代之以一种锐利的、洞察的精光。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又将阿萦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这一次,他的目光更有针对性。他看到了她绾发的那根素银簪子,样式简单,却是实打实的银,说明她并非寻常村姑。他看到了她衣袖的袖口,虽然干净,但边缘处有一点点被磨损的痕迹,那是长时间伏案工作留下的。最后,他的目光,如鹰隼般精准地,落在了她那双手上。
那是一双画工的手。手指纤长,骨节分明。因为常年浸泡清水、研磨颜料,指尖的皮肤显得有些苍白和粗糙。最重要的是,在他修剪得干干净净的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一丝极淡的、像是石青或是赭石的颜色。那颜色,用水洗过很多遍,却依然顽固地留在那里,像一个无法抹去的印记,昭示着主人的身份。
“画工?”他问,语气肯定,不像是在提问,更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阿萦心头一紧。这个人,眼光好毒。她点了点头,没有否认。
“山上的?”他又问。
阿萦再次点头。这龙门山下,除了给佛像作画的,也没什么别的画工了。
“哪位师傅的弟子?”他追问道,身体微微前倾,像是在拉近彼此的距离,无形中施加着压力。
“……王道玄王师傅。”阿萦犹豫了一下,还是报出了师父的名号。王师傅在龙门画工石匠里,也算是一号人物,以严苛和技艺精湛著称,或许能镇住这个看起来有些油滑的年轻人。
果然,听到“王师傅”三个字,小乙“哦”了一声,拉长了音调,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玩味起来。他站直了身体,双手抱在胸前,靠在身后一根棚柱上。
“原来是王大师的高足,失敬失敬。”他嘴上说着客气话,但那眼神和语气,却带着几分毫不掩饰的揶揄。“王师傅的弟子,那可是给佛妆金身的高人。怎么自个儿跑到我这穷乡僻壤的破铺子里来买石头?你们画坊,难道还缺了这点物料不成?还是说……”他故意拖长了音调,那双丹凤眼斜斜地睨着她,“姑娘想买点私房货?”
阿萦不喜欢他这种略带轻佻的语气。她感觉自己像一只被看穿了心思的兔子,浑身不自在。她皱了皱眉,不想回答他这些无关的问题,只是板着脸,又问了一遍:“你这里,到底有没有晕金石?”
“有倒是有。”小乙懒洋洋地说,却丝毫没有要去取货的意思。他伸出一根手指,搔了搔眉毛,“不过嘛,晕金石可是个娇贵东西。它认生。不是什么人,都能用得了它的。”
阿萦心里升起一股恼火。这个人,怎么这么多废话?卖东西就卖东西,还搞这些玄虚,是想坐地起价不成?她耐着性子,冷冷地问:“怎么个娇贵法?”
小乙看她真的生气了,嘴角的笑意反而更深了。他似乎很享受这种逗弄人的乐趣。
“这石头啊,”他故意顿了顿,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性子燥,属火。所以研磨的时候,不能用蛮力,火气一大,石头就‘裂’了,里头的金点会失去光泽,变成一堆死灰。得用凉水,最好是清晨带露水的涧下水,慢慢地、一点点地磨,像哄孩子一样。磨出来的粉,金贵,不能见风。一见风,金点就‘死’了,灵气也就散了。”
他说到这里,又朝阿萦凑近了半步。一股淡淡的、混合着皂角和山野草木的气息,从他身上传来。阿萦下意识地想后退,脚却像生了根一样动不了。
“最要紧的是,”小乙的声音更低了,几乎是在她耳边私语,“用这石头的人,心里不能有火。你心里要是窝着火,带着怨气,手上的颜料也就跟着燥。画出来的东西,甭管是佛还是人,看着再华丽,其实内里一点神韵都没有,邪气得很。”
阿萦听得一怔。
她从未听过这样的说法。师父教她们,只教如何分辨石料的优劣,如何捣、筛、研、漂,如何调配胶水,那些都是可以量化的、有章可循的技法。却从未说过,一块石头,竟然还有“性子”,还有这么多讲究。
她抬起头,看着小乙那双黑亮的眼睛。那双眼睛在槐树的斑驳光影下,闪烁着一种她看不懂的光芒。那光芒里有狡黠,有戏谑,但似乎还有那么一丝丝的……认真。他不像是在胡诌,倒像是在陈述一个他深信不疑的真理。
“你……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她忍不住问。
小乙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又恢复了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样:“我卖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截木头,都跟它聊过天。它叫什么,打哪儿来,脾气怎么样,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心里都有数。”
阿萦觉得这话简直是胡说八道,但看着他身后那满坑满谷、乱七八糟却又似乎各安其位的石头木头,她竟一时无法反驳。或许,它们真的会跟这个奇怪的年轻人说话吧。
她不想再跟他绕圈子了。她从怀里掏出一個小小的布袋,在手里捏了捏,那是她攒了很久的月钱和赏钱,沉甸甸的,是她全部的底气。
“我要看货。”她说,语气坚决,不容置喙。
小乙看着她那副故作镇定的样子,终于笑了笑,没再多说。他转身进了里屋。那里屋光线昏暗,似乎堆满了更多的东西,散发出一股陈旧的、混杂的气味。片刻之后,他捧出一个巴掌大小的、看起来有些年头的木盒子,小心翼翼地放在了门口的货物台子上。
他没有立刻打开,而是先用衣袖,仔细地将盒子上的灰尘拂去。那动作,带着一种郑重。
盒子“啪嗒”一声被打开。
阿萦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盒子里铺着一层柔软的、深蓝色的绒布。绒布之上,静静地躺着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
正是晕金石。
那赭红的底色,温润而沉静,像傍晚时分,太阳落山后,天边最后一抹凝固的火烧云。无数细小到几乎看不见的金色斑点,就深深地蕴藏在这片沉静的红色之中。当小乙的手腕轻微转动,光线的角度发生变化,那些金点便仿佛在石头内部缓缓流淌、游走,变幻出迷离的光晕。
真美啊。
那是一种厚重的、有生命力的美。它不像黄金那样张扬,不像宝石那样炫目。它的华彩,是内敛的,是需要你静下心来,才能感受到的。
阿萦几乎是下意识地伸出手,想去触碰那块石头。
“别动。”
小乙的声音突然响起,短促而有力。
阿萦的手,猛地停在了半空中,离石头只有一寸的距离。
小乙从旁边一个盛着清水的瓦盆里,仔细地洗了洗手,又用一块挂在柱子上的、干净的布巾擦干。然后,他才伸出两根手指,轻轻地、又极其稳地,捏起那块晕金石,将它托在自己的掌心,递到阿萦的面前。
“看可以,”他说,脸上的神情是前所未有的严肃,“别用手摸。人手上有油气,沾上了,会损了它的灵气。”
阿萦的心,没来由地,重重地跳了一下。
她看着他托着石头的手。那是一双做惯了粗活的手,骨节分明,掌心和指腹上,都覆着一层薄薄的茧。但他的手指却很修长,指甲也修剪得干干净净。那块晕金石沉郁的赭红色,映衬着他掌心健康的麦色皮肤,竟有一种奇异的、难以言喻的和谐之感。
她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着一个陌生男子的手。
“多少钱?”她轻声问,目光却还停留在那块石头上,没有移开。
小乙报了一个价钱。
不便宜,但比阿萦预想的,要公道一些。看来他方才那些玄虚之谈,并非只是为了抬高价钱。
阿萦早有准备。她将自己那个小布袋里的铜钱,全都倒在了柜台上。那是她积攒了近两年的体己,一共有八百多文。她蹲下身,开始仔仔细细地点数。她点得很慢,很认真,长长的睫毛垂下来,在脸颊上投下一小片安静的阴影。阳光照在她身上,给她那身朴素的衣衫,也镶上了一道浅浅的金边。
小乙就那么抱着胳膊,靠在柱子上,饶有兴味地看着她点钱。他看着她专注的侧脸,看着她紧紧抿着的嘴唇,看着她灵巧的手指将一枚枚铜钱拨作一堆。
“姑娘,”他突然又开口了,“我多句嘴,你买这块石头,是准备拿回去画佛,还是画人?”
阿萦手上的动作,猛地一顿。
她抬起头,正好对上小乙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那双眼睛,此刻正一眨不眨地看着她,眼神里带着一种洞察一切的了然,和一丝促狭的笑意。
阿萦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了一下。
她感觉自己的脸颊,“轰”的一下,全热了。那个被她藏在箱底最深处的、从未对人言说的秘密,仿佛就这样,被这个初次见面的、油嘴滑舌的年轻人,轻而易举地,窥破了。
她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
她只是慌乱地将点好的钱推了过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几乎是抢一般地,从他手里接过那个装着晕金石的木盒,紧紧地抱在怀里。那盒子,仿佛还残留着他掌心的温度,烫得她心慌。
她转身就走。
“哎,姑娘,找你的钱!”小乙在她身后喊道。
她给的钱,其实是正好的,一文不多,一文不少。
她却像是没听见。她头也不回,脚步匆匆,几乎是逃一般地,离开了那棵大槐树,离开了那间连名字都没有的铺子,也离开了那个目光灼人的年轻人。
她的脸颊在发烫,怀里的木盒也像是有了温度,心跳得像揣了一只兔子。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逃。
只是觉得,那个叫小乙的年轻人,他的目光,比龙门山顶八月的日光,还要灼人。那目光,能穿透石壁,照进人心里最隐秘的角落。
! N2 i7 ^4 C m w+ J) i
2 N% D; E; ]4 |5 j
' C- ]+ W. h" A, q
作者: xiejin77 时间: 2025-8-10 08:12
肆
5 J5 D- t2 E. S2 Q
4 \0 `2 W" e& O7 q. `" U; y+ G" T2 Q8 l( Y2 I/ z: u, i. j2 l- A
[8 B5 U1 m. }( X: D, H I
阿萦是抱着那只小木盒,一路跑回龙门山的。
山路崎岖,她却跑得很快,像是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赶。或许是那个叫小乙的年轻人灼人的目光,或许是自己心底那个被窥破的秘密。她的心跳得厉害,脸颊的热度久久不退,怀里的木盒温温地,像揣了一块刚从火塘里掏出来的炭。
回到山上自己那间简陋的厢房,她才敢停下来,背靠着门板,大口地喘气。屋子里很静,只有窗外山风吹过松林的声音,呜呜地,像远处的叹息。这寂静,是她惯常的陪伴,此刻却让她觉得有些空落落的。她低下头,看着怀里的木盒。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木盒,边角都磨圆了,看得出有些年头。可是在她眼里,它沉甸甸的,装着一个她期盼已久的梦。
她将木盒轻轻放在那张铺着粗布的木床上,没有立刻打开。她先去打了盆清水,仔仔细细地把手洗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指甲缝里再也看不见一丝杂色,才用一块干净的布巾擦干。做完这一切,她才坐回床边,像举行一个极其郑重的仪式,缓缓地打开了盒盖。
晕金石静静地躺在深蓝色的绒布上。
屋内光线昏暗,不比山下日光充足。可即便是在这微弱的光线里,那块石头依旧显露出它独特的华彩。赭红色的石质,像一杯陈年的老酒,沉郁,醇厚。而那些深藏其中的金色斑点,不再流转游走,变得像夜空中的星子,遥远,静谧,却又固执地闪烁着。
阿萦伸出手,指尖在离石头尚有分毫的地方停住了。她想起小乙那严肃的神情和他说的话——“别用手摸。人手上有油气,沾上了,会损了它的灵气。”
她不由得失笑。一块石头,哪来那么多讲究?师父也藏有晕金石,偶尔拿出来给她们看,也没见他这么小心翼翼。这个小乙,故弄玄虚的本事,倒是一流。
可不知为何,她的手,终究是缩了回来。
她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心里却翻江倒海。
小乙那句话,像一根针,扎在她心上最隐秘的地方。“我多句嘴,你买这块石头,是准备拿回去画佛,还是画人?”
他怎么会知道?
她藏在箱底的那卷《神都烟火图》,是她最大的秘密,也是她最大的慰藉。在那些独自一人的深夜,当研磨颜料的疲惫和日复一日的枯燥快要将她淹没时,她就会悄悄点亮一盏油灯,把那幅长卷铺在地上。灯光昏黄,她就趴在冰凉的地面上,用一支最细的笔,一点一点,勾勒出她记忆中的人间。
她画的,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人和事。卖炊饼的汉子,额上全是汗,咧着嘴笑,露出一口黄牙。街角那个补鞋的老头,背驼得像只虾米,手里的针线却走得飞快。还有伊水边洗衣的妇人,用棒槌捶打着衣物,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谣,歌谣顺着水流,飘得很远。
这些人,卑微,劳碌,甚至有些粗俗。他们的面容,被风霜刻上了痕迹;他们的衣衫,沾着尘土和油污。可是在阿萦的笔下,他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都有一种东西。那是一种鲜活的、顽固的、使劲活着的回儿。那种劲儿,是她在石窟里那些宝相庄严、慈悲垂目的佛菩萨脸上,从未见过的。
佛,太远了。远在西天,远在经卷里,远在师父的教诲中。
而人,是近的。近得能闻见他们身上的汗味,能听见他们粗重的呼吸,能感受到他们手掌的温度。
她想把这种“近”画出来。可她笔下的颜色,总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她调出的赭石,能画出皮肤的颜色,却画不出那种被日光晒过、被岁月浸润过的温暖质感。她调出的藤黄,能画出麦饼的焦黄,却画不出那种刚出炉时、热气腾腾的香酥气。
她的画,有形,却缺了一口“气”。那口气,就是人间烟火的气。
她觉得,晕金石,或许能给她这口气。它那沉郁的赭红,是土地的颜色,是生命的底色。而那流转的碎金,是日光,是汗水,是每一个平凡生命里,不为人知的、闪光的瞬间。
她下定决心,要试一试。
她取出自己研磨颜料的家什:一只厚重的石钵,一根光滑的石杵。她没有用作坊里那口大缸里的水,而是提着木桶,走了很远的路,到后山一处人迹罕至的山涧,打了半桶最清冽的涧水回来。水冰凉刺骨,带着草木的清香。
她学着小乙的样子,先将那块晕金石用清水冲洗干净,然后用一把小小的铁锤,极其小心地,将它敲成碎块。每一下,她都用尽了全部的心神,生怕力气大了,真如小乙所说,会把石头的“火气”敲出来。
然后,她将碎石倒入石钵,加了少许涧水,开始研磨。
这活计,她做了五年,早已是深入骨髓的熟稔。可今天,她却觉得手里的石杵,重逾千斤。
她脑子里很乱。
一时是小乙那双黑亮的、仿佛能洞穿一切的眼睛;一时是“半两食铺龙门店”门口那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一时又是师父严厉的面容和“心要净”的教诲。
“用这石头的人,心里不能有火。”小乙的话,像个魔咒,在她耳边反复回响。
她心里有火吗?
她不知道。或许是有的。那是一种不甘的、渴望的、想要挣脱什么的火。她厌倦了这日复一日的清寂,厌倦了给那些没有生命的石像描摹虚假的慈悲。她想画点别的,画点活的、热的、会哭会笑的东西。
这念头,就是一团火,在她心里烧了五年。
“哐啷”一声。
石杵和石钵,发出了一声极其刺耳的碰撞声。她手一抖,力道用得重了。
她赶紧停下来,朝石钵里看去。只见那刚刚磨出少许的赭红色粉末,似乎颜色变得有些暗沉,失去了方才在日光下看到的那种温润光泽。那些细碎的金点,也像是被一层灰蒙住,黯淡无光。
真的……“死”了?
阿萦的心,猛地沉了下去。她愣愣地看着石钵里的粉末,一股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将她牢牢包裹。
原来他没有骗我。
这石头,真的有“性子”。
她忽然觉得很累,一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疲惫。她放下石杵,颓然地坐在地上,抱住自己的膝盖。窗外,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暮色四合,山峦的轮廓变得模糊,像一幅褪了色的水墨画。远处的佛钟响了,一声,又一声,悠远,苍凉。
在这钟声里,她忽然很想念山下那个吵闹的、混乱的、人声鼎沸的集市。
她想念那股子浓郁的、混杂着各种气味的空气。想念那碗能把五脏六腑都烫得舒坦的羊肉汤。甚至,想念那个说话油腔滑调,眼神却比谁都清亮的年轻人。
在山上,她是王师傅的高足,是给佛妆金身的画工阿萦。她需要净手,净心,摒除杂念。
可是在山下,在那短暂的片刻里,她好像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会为了一块石头讨价还价、会被人的目光看得脸红心跳的、饥肠辘辘的姑娘。
她忽然很想再去做一回那个姑娘。
哪怕只有一个时辰也好。
第二天,她以“颜料用尽,需下山采买”为由,又向师父告了一天假。师父有些不悦,但也没多说什么。或许是她脸色太差,看起来像生了一场大病。
这一次下山,她没有直接去“静心斋”。她先去了伊水边。
正是清晨,河上起了薄雾,水面像一块巨大的、未曾打磨的灰玉。有早起的渔船,划破了这片静谧,船桨“欸乃”一声,在水上荡开一圈圈涟漪。岸边的柳树,垂下千万条绿丝绦,上面挂满了晶莹的露珠。
她脱下鞋,赤着脚,踩在河边湿润柔软的泥沙上。水很凉,激得她脚底微微刺痛,但那股凉意顺着血脉往上走,却让她混乱的头脑,清醒了几分。
她就那么沿着河岸,慢慢地走。走过码头,看见那些光着脊背的纤夫,正喊着号子,将一艘巨大的货船,从浅滩里,一寸一寸地,拉向深水。他们的号子,苍凉而有力,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膛里吼出来的。汗水和河水,混在一起,在他们古铜色的皮肤上,闪着光。
她心里忽然有了一丝明悟。
小乙说,心里不能有火。或许,不是不能有火,而是那火,不能是窝在心里的、无处发泄的燥火。
纤夫们心里也有火。那是与天斗、与水斗、为了生计而迸发出的、最原始的生命之火。可他们的火,都吼进了号子里,融进了汗水里,使在了那根沉重的纤绳上。所以,他们的火,是通透的,是有力量的,是不会把人烧坏的。
而她的火呢?一直被她死死地压在心底,不敢示人。那火,烧不着别人,最终,只会烧伤自己。
她好像有点明白,该如何去磨那块晕金石了。
也明白,自己现在最该去的地方,是哪里。
她转过身,朝着那个热闹的、能把所有心事都煮沸化掉的地方,走了过去。
“半两食铺龙门店”。
# J% j5 Y" z' ~/ a9 j) G
3 i: |" _& C: P. T& I. ]/ R9 O# t C
5 Q( R2 l v7 R' i
作者: xiejin77 时间: 2025-8-11 07:52
伍
0 ]# |) N! G6 f9 |. L
3 z0 L$ g0 q6 e9 D
/ A. X) C! ~6 d* V" C) e/ w/ K' j# J8 }# z# K, K% l) @
“半两食铺龙门店”的早晨,是从一口巨大的汤锅里开始的。
天还未亮透,老板老王就已经起身。他光着膀子,只在腰间围一条油腻的布裙,露出圆滚滚的、像弥勒佛一样的肚子。他熟练地将昨夜就已经泡去血水的大块羊骨、羊排,投入那口能煮下一整只羊的大铁锅里,加上拍碎的姜块、几粒草果和一撮花椒,然后用巨大的木瓢,一瓢一瓢地,将井水添满。
灶膛里的火,是老火。用的是最耐烧的硬木,火苗舔着锅底,不疾不徐。水开了,老王就拿着一把巨大的铁勺,一遍遍地,撇去浮沫。那动作,极有耐心,像个绣花的姑娘,不放过一丝一毫的杂质。直撇到汤色清亮,才盖上锅盖,转为文火,让那锅汤,在时间的催化下,慢慢地,释放出最醇厚的味道。
等到日上三竿,集市彻底热闹起来的时候,那锅汤,也就熬好了。汤色奶白,像上好的羊脂玉,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金黄色的油花。一股浓郁得近乎蛮横的香气,从锅里升腾起来,盘踞在食铺上空,像一面无形的旗帜,召唤着四面八方的饿鬼。
阿萦就是被这面“旗帜”召唤来的。
她到食铺门口时,四五张桌子,已经坐得满满当当。来这里吃饭的,大多是些干力气活的汉子。码头的船工、山上的石匠、过路的脚夫。他们对吃食的要求很简单:量大,油足,热乎。能用最少的钱,填饱肚子,给接下来的劳作,攒足力气。
老王正在人群中穿梭,嗓门洪亮,记性极好。
“张三哥,一碗羊肉汤,多放肉,多搁辣子!”
“李二叔,老规矩,一碗羊杂,不要肺,多来点肠!”
“好嘞!您擎好吧!”
他手脚麻利,一边应着,一边从滚开的汤锅里捞出烫好的羊肉羊杂,在案板上“唰唰唰”几刀切成薄片,抓进大陶碗里,浇上一勺滚烫的奶白原汤,再依着客人的口味,撒上碧绿的芫荽、雪白的葱花,或是淋上一勺自家炼的、红得发亮的羊油辣子。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汤,就这么被端上了桌。
食客们也顾不上说话,一个个埋着头,呼噜呼噜地,喝汤,吃肉,就着刚出炉的胡饼。那声音,此起彼伏,像一首热闹而质朴的交响乐。汗水顺着他们的额角往下淌,混着汤的热气,蒸腾起一片白茫茫的雾。
阿萦站在食铺门口,有些手足无措。
她一个身形纤细、衣着干净的年轻姑娘,站在一群光着膀子、浑身汗味的糙汉子中间,显得格格不入。像一滴清水,掉进了滚油锅里。所有人的动作,都像是停顿了一下,几十道混杂着好奇、探究的目光,齐刷刷地朝她射了过来。
她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下意识地想转身逃走。
“姑娘,里边坐!”
老王那洪亮的声音,替她解了围。他从人堆里挤出来,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用肩上那块看不出本色的布巾擦了擦手,指了指角落里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那桌子,靠着墙,相对僻静一些。
“想吃点什么?小店的羊肉汤,可是龙门山一绝!”
阿萦定了定神,低着头,快步走到那张桌子边坐下。桌面上还残留着上一位客人留下的油渍,她却顾不上了。
“一碗……一碗羊肉汤,”她小声说,声音细得像蚊子叫,“再……再要一个胡饼。”
“好嘞!姑娘您稍等!”
老王应了一声,转身去了。周遭的食客们,见没什么热闹可看,也便收回了目光,继续埋头于自己的碗中。那热闹的呼噜声,又重新响了起来。
阿萦稍稍松了口气。她挺直了背,坐在长凳上,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她不敢四处张望,只能看着自己面前那张油腻的、被岁月磨得光滑的木桌。桌面上,有刀砍的痕迹,有碗底烫出的圆形印子,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早已干涸的深色污渍。
这一切,都和山上那间一尘不染的斋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斋堂里,用饭要止语,碗筷不能发出声音,一粒米都不能剩下。那里,吃饭也是一种修行。
而在这里,吃饭,就是吃饭。是为了活着,为了有力气。那种原始的、坦荡的生命欲望,就这么赤裸裸地、热气腾腾地,摆在你的面前。
很快,一碗汤,一个饼,被端了上来。
汤碗是粗陶的,很烫手。奶白的汤上,飘着几片切得极薄的羊肉,和一大撮碧绿的芫荽。胡饼是刚从隔壁张二哥的吊炉里取出来的,表面焦黄酥脆,洒满了烤得香喷喷的白芝麻。
一股浓郁的香气,直往阿萦的鼻孔里钻。她的肚子,不争气地,又叫了一声。
她学着周围人的样子,把胡饼掰成小块,泡进汤里。然后,她拿起那把沉甸甸的、缺了个口的瓦勺,舀了一勺汤,小心翼翼地,送进嘴里。
那一瞬间,阿萦觉得自己浑身的毛孔,都舒张开了。
好烫!
好鲜!
那是一种极其醇厚、极其直接的味道。羊肉的鲜,大骨的香,芫荽的清爽,还有那一丝丝若有若无的胡椒的辛辣,在她的舌尖上,猛烈地爆炸开来。那味道,顺着喉咙滑下去,像一道温暖的洪流,瞬间就冲刷了她所有的五脏六腑。
她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山上的饭食,清淡,素净,是为了“净心”。而这一碗汤,却像是为了“暖心”而生的。它能把你从里到外,都烫得服服帖帖,让你觉得,活着,真是一件踏实而温暖的事情。
她再也顾不上什么仪态,也学着那些汉子,埋下头,一口汤,一口饼,大口地吃了起来。
汤很热,她吃得鼻尖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有几缕碎发,被汗水打湿,黏在了她的额角。她却浑然不觉。她的世界里,只剩下眼前这一碗汤。
她吃得很专心,很投入,像是在完成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直到一个声音,在她头顶响起。
“姑娘,汤的味道,还行?”
阿萦猛地一抬头。
一张年轻的、带着促狭笑意的脸,出现在她眼前。眉毛很浓,眼睛是狭长的丹凤眼,眼珠黑得发亮。
是小乙。
他不知什么时候,坐到了她对面的长凳上。他也叫了一碗汤,却没有动,只是双手搁在桌上,好整以暇地看着她。
阿萦嘴里还塞着半块泡软了的胡饼,脸“轰”的一下,又红了。她手忙脚乱地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差点噎着,呛得她连连咳嗽,眼泪都快出来了。
小乙见她这副狼狈的模样,嘴角的笑意更浓了。他也不说话,只是从桌上的筷笼里,抽出一双筷子,用自己的袖子擦了擦,递到她面前。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他说,声音里带着笑。
阿萦接过筷子,窘迫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她胡乱地点了点头,低下头,再也不敢看他,只用勺子,一下一下地,漫无目的地搅着碗里的汤。
“昨天跑那么快做什么?”小乙像是闲话家常一样,随口问道,“我还以为我铺子里的东西,是偷来的抢来的呢。”
阿萦的脸更红了,头埋得更低。
小乙也不逼她,自顾自地拿起勺子,喝了一口汤,发出一声心满意足的叹息。
“还是老王家的汤,地道。这汤啊,妙就妙在火候上。少一分,味道出不来;多一分,汤就浊了。跟你们画画,是不是一个道理?”
阿萦搅动汤勺的手,微微一顿。
她抬起眼,悄悄地看了他一眼。他正专心致志地对付着碗里的汤,侧脸的线条在食铺嘈杂的光影里,显得干净而利落。他吃东西的样子,和周围那些汉子一样,不讲究什么仪态,却透着一股子对食物最质朴的敬意。
“那块石头,”他又像是想起了什么,抬起头,看着她,那双黑亮的眼睛,在蒸腾的热气里,显得格外有神,“回去磨了?”
阿萦的心,咯噔一下。她握着勺子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
她点了点头。
“磨得如何?”他追问。
阿萦咬了咬嘴唇,摇了摇头。
“我就知道。”小乙一点也不意外,反而笑了,那笑容里,带着几分“果然如此”的得意,“你心里有事,手上的劲儿就不对。那石头是有灵性的,你骗不了它。”
“一块石头,哪有什么灵性……”阿萦忍不住小声反驳。
“怎么没有?”小乙把勺子往碗里一放,发出“当”的一声脆响。他身子微微前倾,看着阿萦,眼神忽然变得认真起来,“万物皆有灵。这碗汤有灵性,这张桌子有灵性,你手里的笔,你画的画,都有。你信它,它就回馈你;你不信它,它就是一块死物。”
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块石头,投进了阿萦心里那片本已混乱的湖水中,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万物皆有灵。
这话,她似乎在哪里听过。不是在师父的课堂上,而是在那些更古老的、关于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里。那是一种极其朴素,又极其浪漫的道理。
她看着小乙。他明明是个油嘴滑舌的商人,说起话来,却又带着一种近乎于哲人的笃定。他身上的气质很奇怪,一半是市井的烟火气,一半又是山野的脱俗气。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在他身上,奇异地融合在了一起,毫不违和。
“那你说,”阿萦鬼使神差地,问出了口,“我该怎么磨?”
小乙笑了。他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下巴指了指她面前那碗快要见底的汤。
“你先把汤喝完。”他说,“喝完了,我带你去个地方。”
阿萦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她还是顺从地,端起那只粗陶大碗,将剩下的一点汤汁,连带着泡软的饼块和肉末,一饮而尽。温暖的汤水滑入腹中,一股暖意,从丹田升起,流遍四肢百骸。那种踏实而满足的感觉,冲淡了她连日来的焦躁和不安。
她放下碗时,小乙也正好喝完了最后一口汤。他从怀里掏出几枚铜钱,往桌上一扔,对着炉灶那边喊了一声:“老王,钱放桌上了!”
然后,他站起身,对着还有些发愣的阿萦,一扬下巴。
“走吧。”
他转身就走,那件洗得发旧的蓝色短衫的背影,很快就汇入了集市嘈杂的人流之中。阿萦犹豫了一下,还是起身,快步跟了上去。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着他走。
只是觉得,这个奇怪的年轻人身上,或许藏着她想要的答案。
& |! f( s' h6 |4 c
* L3 [! Y0 N7 P
, K! @+ m6 J9 i# S) ~$ x
作者: xiejin77 时间: 2025-8-11 16:50
陆' V2 `! h( E, h* Q( O
0 Q$ {9 ^4 j! M+ x! S0 N0 r- N小乙领着阿萦,并未走向市集深处那些贩卖奇珍异宝的店铺,也未走向文人雅士流连的茶馆酒肆。他转了个方向,朝着与龙门山隔伊水相望的、那片更加荒僻的东山走去。
他们穿过了喧闹的“静心斋”,身后的鼎沸人声与食物香气渐渐被风吹散,像一场退潮的梦。脚下的路,也从平整的石板,变成了崎岖不平的土路。路边是半人高的、茂盛的野草,草叶上还挂着清晨的露水,沾湿了阿萦的裙角,带来一阵清凉的草木气息。
阿萦心中充满了疑窦,却没有开口问。她只是默默地跟在小乙身后,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她看着他那件洗得发旧的蓝色短衫的背影,在清晨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挺拔。他步履轻快而稳健,对这条路显然极其熟悉,哪里有坑洼,哪里有碎石,他都避得恰到好处。
走了约莫一炷香的工夫,他们来到了一处废弃的采石场。
这里显然已经荒废了许久。巨大的、被开凿了一半的石壁,像一道道狰狞的伤疤,裸露在山体之上。四处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废弃石料,有的棱角分明,有的已经被风雨磨去了棱角,长满了青苔。整个山谷,寂静得能听见风的声音,和自己心跳的声音。
小乙在一块巨大的青石上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微微有些气喘的阿萦。
“到了。”他说,脸上带着一丝神秘的笑容。
“这里……是什么地方?”阿萦环顾四周,眼中满是困惑。这里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是那种最粗糙、最没有生命的顽石。
小乙没有回答,而是走到一块半人高的废石前。那石头质地粗劣,表面满是裂纹和杂色,是石匠们最先抛弃的“废料”。他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石头冰凉的表面,那动作,像是在安抚一头沉睡的野兽。
“你觉得,”他头也不回地问,“这块石头,它在想什么?”
阿萦一愣,觉得这个问题简直荒谬至极。“石头……不会想东西。”
“错了。”小乙转过头,那双黑亮的眼睛在阳光下,闪烁着一种近乎于顽固的、笃定的光芒。“它在等。”
“等什么?”
“等一个能看懂它的人。”小乙说着,从腰间解下一个布包。布包打开,里面是几把大小不一的、看起来有些年头的鏨子和一柄沉重的铁锤。他选了一把最细的尖头鏨,又拿起铁锤,对阿萦说:“你站远些。”
阿萦依言退后了几步,不解地看着他。
小乙深吸了一口气。他没有立刻动手,而是闭上眼睛,将一只手掌,轻轻地贴在那块石头上。他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仿佛在用掌心的温度,与这块沉睡了不知多少年的顽石对话。山风吹过,扬起他额前的发丝,那一刻,他的身上,竟然没有了半分市井商人的油滑之气,反而透出一种工匠特有的、与物同化的沉静与专注。
片刻之后,他睁开眼。眼神清亮,如山泉洗过。
他举起了锤子。
“当!”
第一声,清脆,短促。鏨子准确地落在了石头表面一条极其细微的天然裂纹上。
“当!当!当!”
锤击声变得富有节奏。他不急不躁,每一锤的力道,都控制得恰到好处。石屑纷飞,在他脚下积了薄薄的一层。他的动作,看起来并不费力,更像是在顺应着什么。他不是在用蛮力对抗石头的坚硬,而是在寻找它内在的纹理,顺着它的“性子”,将它层层剥开。
阿萦看得有些痴了。
她从未见过这样解石的。山上的石匠们,开山凿佛,讲究的是大开大合,气势磅礴。而小乙的动作,却细腻得像是在绣花。他手里的锤子和鏨子,不像工具,更像是他手臂的延伸。
渐渐地,那块石头粗糙的外皮,被一点点剥落。露出了里面相对细腻的石质。那石质,呈现出一种温润的、介于青白之间的颜色。最奇妙的是,随着外层石皮的脱落,石头内部,竟然显露出一些片、一团团,如同水墨晕染开的、深浅不一的黑色纹理。
那些纹理,浑然天成,姿态万千。有的像远山含黛,有的像古木寒鸦,有的又像狂草大家醉后挥洒的笔触,恣意纵横,气韵生动。
小乙的锤声停了。
他扔下工具,用袖子擦了擦额上的汗,然后退后两步,欣赏着自己的“作品”。那块原本其貌不扬的废石,此刻,竟像一幅立体的、未经人力雕琢的水墨画,静静地立在那里。
“现在,”小乙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得意的喘息,“你再看它,它还是一块死物吗?”
阿萦说不出话来。
她怔怔地看着那块石头,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她终于明白小乙带她来这里的用意。
他不是在教她任何具体的技法。他是在教她一种“看”的方式。
“每一块石头,每一截木头,都有它自己的纹理,自己的脾气,自己的‘心’。”小乙走到她身边,声音恢复了平静,“你若只是把它当成一块没有生命的材料,用蛮力去对付它,它给你的,自然也是死的。你得先懂它,顺着它,把它心里藏着的东西,帮它‘请’出来。你对它温柔,它才能还你神韵。”
他转头看着阿萦,眼神诚挚:“你的那块晕金石,也是一样。你心里的火,太燥了,太急了。你只想著从它身上索取你要的颜色,却没想过,它想告诉你什么。”
阿萦的心,被这句话狠狠地刺了一下。
是啊。她一直觉得,是自己需要晕金石,来完成她的画。却从未想过,那块石头,或许也在等待一个能读懂它的人。
“我……”她张了张嘴,却不知该说什么。
“你心里的那团火,没有错。”小乙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语气变得柔和起来,“想画那些活生生的人,想画这人间的烟火气,没有错。错的是,你把这团火,当成了自己的私心,当成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偷偷摸摸地藏着,压着。火被压久了,就变成了邪火,燥火。它不舒畅,你手上的活儿,自然也就不舒畅。”
他指了指远处伊水上那些拉船的纤夫,又指了指“半两食铺龙门店”的方向:“你看那些纤夫,他们吼号子,就是把心里的火,吼出来。老王熬汤,就是把对食物的敬意,熬进汤里。他们活得坦荡,所以他们身上的那股子劲儿,是通透的,是暖的。”
“阿萦姑娘,”他第一次,这样郑重地叫她的名字,“你的火,也该找个地方,痛痛快快地点起来。不是偷偷摸摸地在心里烧,而是正大光明地,在你的笔尖上,在你的画布上,烧给它自己看。”
阿萦抬起头,看着小乙。
清晨的阳光,给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边。他的眼睛里,没有了平日的狡黠和戏谑,只有一片澄澈的、温暖的真诚。那真诚,像一双温厚的手,轻轻地,拂去了她心头积攒多年的尘埃。
她忽然觉得,自己一直以来,都错了。
她敬畏佛国的清净,却又贪恋人间的喧嚣。她以为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东西,是罪过,是杂念。所以她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分开。在山上,她是无欲无求的画工;在山下,她是心怀秘密的凡人。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矛盾体,左右为难,不得安宁。
可小乙却告诉她,这一切,本就是一体的。
没有那些活生生的、在尘世中挣扎哭笑的凡人,又哪里来那普度众生的、慈悲含笑的佛?烟火气,并非神佛的对立面,或许,它本就是神性最真实的根基。
“谢谢你,小乙。”
她轻声说。这句话,发自肺腑。
小乙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又恢复了那副爽朗的模样:“谢什么?我一个卖石头的,胡说八道罢了。道理懂了,肚子也该饿了。走,我请你吃点东西去。不过这次,可不是羊肉汤了。”
I+ N7 K& n# z6 ?) M- J: P1 K* D" c9 j+ C
: L. B" u" T, n9 m3 z6 u) I+ p
作者: xiejin77 时间: 2025-8-12 11:02
柒3 ^6 {1 v' z2 z$ F
4 T# x, w0 O% j: e% v ~小乙没有带阿萦回“半两食铺龙门店”。他领着她,钻进了“静心斋”旁边一条更为狭窄、更具生活气息的小巷。
巷子两旁,是栉比鳞次的民居。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晾晒着衣物,挂着干辣椒和蒜头。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复杂而安逸的味道:饭菜的香气、皂角的清香、还有泥土和阳光的味道。有孩童在巷子里追逐打闹,有妇人坐在门槛上纳着鞋底,时不时地高声训斥一句,引来一阵嘻笑。
这一切,都和阿萦那幅《神都烟火图》里的场景,如此相似。可此刻亲身走在其中,她才感觉到,画纸上的,终究是静止的,而眼前的这一切,是流动的,是鲜活的,是带着温度的。
小乙在巷子深处一户人家的门前停下。那是一户极其普通的人家,甚至显得有些破旧。他熟门熟路地推开那扇虚掩着的柴门,高声喊道:“刘大娘,我带客人来了!”
一个头发花白、身形微胖的老妇人,应声从屋里走了出来。她脸上布满了皱纹,但笑容却极其和蔼可亲。她看见小乙,脸上笑开了花:“是小乙啊!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当她看见跟在小乙身后的阿萦时,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变成了然的、慈爱的笑。
“这位是……?”
“我朋友。”小乙大大方方地介绍道,然后转头对阿萦说,“这是刘大娘,她做的米糕,是这附近最好吃的。”
刘大娘热情地将他们让进屋里。屋子很小,陈设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张半旧的八仙桌,擦得油光发亮。小乙让阿萦坐下,自己则像在自己家一样,跑去灶房,帮着刘大娘端出了一碟热气腾腾的米糕,和两碗新沏的粗茶。
那米糕,是用最普通的糯米做的,上面点缀着几颗红枣。没有精致的造型,也没有华丽的颜色,只是散发着一股最质朴的、糯米的清香。
“姑娘,快尝尝,趁热吃。”刘大娘笑呵呵地说。
阿萦拿起一块。米糕还很烫,软糯香甜,带着红枣的甘甜。那是一种很简单,很家常的味道,却让她觉得,心里某个地方,被轻轻地填满了。
“刘大娘的儿子,是山上有名的石匠。”小乙一边吃着米糕,一边对阿萦说,“前些年,在山上凿佛的时候,不小心伤了腰,干不了重活了。现在就在家里,帮着大娘做点小营生。”
正说着,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从后院走了出来。他身形高大,但走路的姿势,却有些僵硬,显然是腰上有旧伤。他看到小乙,憨厚地笑了笑:“小乙哥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个刚刚做好的、小小的木雕。那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牧童,造型稚拙,线条粗犷,却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生动和野趣。
“手艺又进步了啊,刘大哥。”小乙拿起那个木雕,赞叹道。
那汉子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瞎鼓捣罢了,比不上你们这些正经的手艺人。”
阿萦看着那个木雕,又看了看那个因为受伤而无法再挥锤凿石的汉子,心中忽然一动。她想起了自己,因为一次评判,就被剥夺了画笔的画工。
他们吃完了米糕,告别了热情的刘大娘母子,重新走在阳光下。
“那个刘大哥,”阿萦轻声问,“他以前……一定是很厉害的石匠吧?”
“是啊。”小乙点了点头,语气里带着一丝感慨,“奉先寺那尊卢舍那大佛,你知道吧?他爹,就是当年主持开凿的总匠师。他也跟着他爹,在那里干了十几年。可惜了。”
阿萦沉默了。她似乎能想象到,一个技艺超群的石匠,却再也无法拿起锤子,只能在自家的后院里,雕刻一些小玩意儿来慰藉心灵,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失落。
“可我觉得,”小乙忽然又笑了,“他现在,比以前快活。”
“为什么?”
“以前,他是为皇家、为佛祖凿石头。石头是功德,是任务,是千钧重担。现在,他是为自己、为高兴雕木头。木头是乐子,是玩意儿,是手心里的小确幸。”小乙看着阿萦,眼神深邃,“阿萦姑娘,有时候,画什么,雕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为谁而画,为谁而雕。”
阿萦的心,又被重重地敲了一下。
为谁而画?
过去,她是为师父而画,为那份活下去的恩情而画。后来,她是为自己心底那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而画。可这两种,都让她活得分裂而痛苦。
或许,还有第三种可能。
不为别人,也不仅仅为自己。而是为了那画本身,为了那份将心中所感、眼中所见,付诸笔端的、最纯粹的快乐。
回到山上,已是傍晚。
阿萦没有回自己的厢房,而是直接去了存放颜料的工坊。她点亮一盏油灯,将那只装着晕金石的木盒,郑重地放在了石钵旁。
这一次,她没有急着动手。
她静静地坐着,闭上眼睛。脑海里,不再是师父严厉的面容,也不是小乙戏谑的眼神。她想着的,是废弃采石场那块顽石内部,如水墨般晕开的纹理;是刘大娘递过来的那块热气腾腾的米糕;是那个憨厚石匠手中,那个充满生趣的牧童木雕;是“半两食铺龙门店”里,那碗能把五脏六腑都烫得舒坦的羊肉汤。
她想着那些纤夫苍凉的号子,那些妇人爽朗的笑声,那些孩童清脆的啼哭。
这些,都是人间的烟火。卑微,却温暖。短暂,却真实。
她心里那团被压抑了许久的火,不再左冲右突,寻找出口。它找到了自己的河道,开始平静而有力地,流淌起来。
她睁开眼,眼神清澈而宁静。
她将晕金石投入石钵,加入清冽的涧水,拿起了石杵。
这一次,她磨得很慢,很稳。石杵在石钵里,画着一个又一个圆。她不觉得累,也不觉得枯燥。她的心神,完全沉浸在这重复的、单纯的动作里。她感觉自己不是在研磨一块石头,而是在与它对话。
她能感觉到,石头坚硬的质地,在水的浸润和石杵的压力下,一点点地软化,释放出它内心深处最温暖的颜色。
不知过了多久,当她将最后磨好的颜料倒出来时,整个工坊,仿佛都亮了一下。
那颜色,盛在洁白的蚌壳里,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心醉的美。它不再是单纯的赭红色,而是一种温暖的、厚重的、仿佛还带着生命余温的赤金色。那些细碎的金点,均匀地悬浮在膏脂般细腻的颜料里,像无数颗微小的太阳,散发出柔和而璀璨的光晕。
这,才是晕金石真正的颜色。是土地的厚重,与日光的华彩,最完美的融合。
阿萦知道,她的《神都烟火图》,终于等来了它最需要的那一抹颜色。
; q2 E* |+ q5 ]. ?& C8 } K
* v! Y7 q+ M5 B2 Q
G: D8 g) r9 [. X2 O; T
作者: xiejin77 时间: 2025-8-14 10:14
捌
# W) w+ V! \* }- z: P) d3 w. B" `- u, W" f( T+ v
4 o( v( \1 o8 k8 E% p
O F! S' l' L) t: r) @# h
接下来的日子,阿萦的生活,似乎恢复了往常的轨迹,却又在内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白天,她依旧是龙门山上那个沉默寡言、勤勉细致的画工。她研磨颜料,修补壁画,给新凿的佛像敷彩。只是,她的心境,完全不同了。
她不再觉得这份工作是枯燥的修行,也不再将佛国与人间,割裂成两个对立的世界。她看着石壁上那些慈悲垂目的菩萨,会想起刘大娘脸上和蔼的皱纹。她为金刚力士描摹愤怒的眉眼时,会想起伊水边那些为了生计而搏命的纤夫。她为飞天仙女的衣袂染上绚烂的色彩时,会想起集市上那些穿着花布袄裙、笑语嫣然的少女。
她发现,神性与人性,原来是相通的。那些极致的慈悲、愤怒、喜悦,都可以在凡人的脸上,找到最真实的影子。她的笔,因此变得更加生动,也更加笃定。她笔下的线条,依旧精准,却多了一丝人情的温度。她调配的色彩,依旧华丽,却多了一份岁月的厚重。
连一向对她要求严苛的师父王道玄,也察觉到了她的变化。他偶尔会站在她身后,看她作画,眉头紧锁,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他能感觉到,阿萦的画,不一样了。那是一种他说不出来的、微妙的变化。画还是那样的画,技法还是那些技法,但画里,似乎多了一口“气”。一口活的气。
这让王道玄感到欣慰,同时,又隐隐有一丝不安。他信奉的是古法,是规矩。画佛,最重法度,不可有半分逾越。阿萦的画,正在一种他无法掌控的边缘游走。那种鲜活的气息,让他觉得动人,却也让他担心,会不会有一天,失了分寸,落入“凡俗”的窠臼。
而到了夜晚,当万籁俱寂,山上只剩下风声和松涛声时,阿萦的世界,才真正开始。
她会锁好房门,点亮那盏小小的油灯,将那卷《神都烟火图》,小心翼翼地铺在地上。那幅长卷,已经画了近三分之一。在昏黄的灯光下,一个活色生香的神都市井,正在她的笔下,一点点地,被唤醒。
她用那新磨出的晕金石颜料,为画里的人物,敷上肌肤的颜色。
她画“半两食铺龙门店”的老板老王。用晕金石调和赭石,画出他那被烟火熏得油亮的、红光满面的脸膛。再用极淡的金粉,点在他额头沁出的汗珠上,那汗珠,便立刻有了滚烫的温度。
她画那个坐在门口,埋头喝汤的脚夫。用晕金石混合些许土黄,画出他那被风霜和烈日侵蚀得粗糙皴裂的皮肤。那皮肤,不再是平面的颜色,而有了质感,有了温度,有了生命经年累月留下的印记。
她甚至在食铺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画了一个年轻人的背影。那人穿着一件蓝色的短衫,正咧着嘴,露出一口白牙,像是在跟对面的人说着什么有趣的话。她没有画他的脸,只画了他被阳光照亮的、健康的麦色脖颈,和那几缕不听话地垂落的黑发。她用最淡的晕金石颜料,轻轻地、一遍遍地渲染,直到那片肌肤,透出温暖的光晕。
每当画到这里,她的心跳,就会没来由地,快上几分。
她下山的次数,也变得多了起来。
她不再需要用“采买物料”这样蹩脚的借口。她会利用午间休息的短暂空隙,或者是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之后,迎着夕阳,快步下山。
她会先去小乙的铺子。铺子还是那个样子,乱糟糟的,却乱得有章法。小乙也还是那个样子,大部分时间,都懒洋洋地靠在棚柱上,看着人来人往。但当他看见阿萦的身影出现在那棵大槐树下时,他那双本来有些眯着的丹凤眼,总会立刻亮起来。
他们的对话,总是从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开始。
“今天有什么新鲜货色?”阿萦会装作不经意地问。
“刚从终南山弄来几块鸡血石,要不要看看?”小乙会笑嘻嘻地回答,然后献宝似的,捧出一個盒子。
他们会就着一块石头的成色、一截木头的纹理,聊上很久。小乙总能说出许多稀奇古怪的道理,他说木头分公母,石头有魂魄。阿萦一开始觉得是胡说,听得多了,竟也觉得,他说的,似乎有几分道理。
有时候,阿萦也会把自己新画的一些小稿,带给他看。那是一些画在废弃纸张上的、不成章法的速写。一朵被雨打湿的野花,一只停在树枝上打盹的倦鸟,或是一个打着哈欠的货郎。
小乙会看得极其认真。他不像师父那样,先看笔法,再看构图。他看的,是画里的“意思”。
“这只鸟,画得好。”他会指着那幅速写说,“你看它缩着脖子的样子,一看就是昨晚没睡好,被窝让别的鸟给占了。”
他总能用他那套歪理,把画里的东西,说得活了过来。阿萦常常被他逗得忍不住笑。那笑声,清脆,明亮,是她在山上,从未有过的。
他们的交流,很少涉及彼此的过往。阿萦不知道小乙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流落到神都,做一个卖石头木头的小商人。小乙也从不问阿萦,为什么一个好好的画工,偏要偷偷画那些市井百态。
他们之间,有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他们都懂得,有些东西,是属于过去的。而他们所共享的,是当下。是那块石头的温润,是那幅画的生趣,是那棵大槐树下,斑驳的阳光和安逸的午后。
当然,他们最常去的地方,还是“半两食铺龙门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食铺角落里那张靠墙的桌子,成了他们的专属座位。只要他们一来,正在埋头喝汤的熟客们,就会识趣地,挪到别的桌子去,还会朝他们挤眉弄眼地笑。
老板老王,更是乐见其成。他总会把最大块的羊肉,盛在他们的碗里,还会多送一碟自家腌的爽口小菜。
“小乙,你小子,可算开窍了!”老王会用他那洪亮的嗓门,毫不避讳地打趣道,“这么好的姑娘,你要是再不抓紧,当心让城里那些油头粉面的公子哥给拐跑了!”
每到这时,小乙就会嘿嘿一笑,也不反驳。而阿萦,则会把脸埋进那只巨大的汤碗里,假装专心喝汤,耳朵却红得像要滴出血来。
食铺里的人声鼎沸,汤锅里升腾的热气,混杂着羊肉和芫荽的香气,将他们包裹其中。在这片温暖而嘈杂的烟火气里,阿萦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和踏实。
她和他的关系,就像老王锅里那文火慢炖的汤。没有惊心动魄的开场,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一点点地,将彼此的味道,熬进自己的生命里。那滋味,醇厚,绵长,暖到骨子里去。
6 T( \) o% O; o) U: n1 j0 B6 g# j, [- ], b
) C$ Z* h$ y+ S. a, ~, b
作者: xiejin77 时间: 2025-8-15 11:59
玖
* N2 l+ t& r3 D4 y. I" w# K5 u
* c1 U5 L0 q+ O0 J- @7 t3 m, c9 V6 H1 l/ V! @
0 B2 A/ L. s2 l8 B9 B5 n
秋意渐浓,龙门山的枫叶,一夜之间,就红透了半边天,像打翻了的朱砂。伊水的水面,也变得更加澄澈,倒映着碧蓝的天和流动的云,像一块巨大的琉璃。
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是一个检验成果的季节。
这天,师父王道玄将阿萦叫到了宾阳南洞。
宾阳三洞,是龙门石窟开凿年代较早的北魏时期洞窟,风格古朴雄健。南洞的主佛阿弥陀佛,端坐中央,宝相庄严。而左右两侧的胁侍菩萨,身形修长,面容清秀,带着一种超凡脱俗的宁静之美。历经百年风雨,左侧那尊胁侍菩萨的面相,已经有些斑驳,尤其是脸颊和眼角的敷彩,脱落得尤为严重,使得那份宁静,平添了几分沧桑。
“这尊菩萨,”王道玄指着那尊半旧的佛像,对阿萦说,“将作监下了令,要在霜降之前,修补完成。监正大人,点了你的名。”
阿萦心中一凛。
将作监监正,是整个画坊工匠的最高官长。能被他点名,是天大的荣耀,也意味着,这是一项绝不容有失的重任。
“弟子……怕难当此任。”阿萦垂下头,谦逊地说。这并非完全是客气话。这尊菩萨的风格,是典型的秀骨清像,讲究的是神韵的飘逸和内在的静气,对画工的心性和技艺,要求极高。
“我相信你。”王道玄的声音,难得地带上了一丝温和。“你近来的画,进境很大。那股子‘气’,提上来了。为师知道,你常下山。为师不反对。佛法,不在山之高低,而在人心之内外。你若能将那山下的人间气,化为笔下的佛性,那便是你的造化。”
阿萦猛地抬起头,震惊地看着师父。
她没想到,自己那些小心思,师父竟然全都看在眼里。他非但没有责备,反而给予了她一种她从未奢望过的理解和肯定。
“师父……”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去吧。”王道玄拍了拍她的肩膀,语气又恢复了往日的严肃,“记住,法度之内,方见真章。莫要失了分寸。”
“是,弟子明白。”阿萦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一次,她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斗志和信心。这不仅仅是一项任务,更是师父给予她的一次机会,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她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次修补工作中。
她把自己关在宾阳南洞里,一待就是一整天。她先是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什么也没做,只是坐在脚手架上,静静地,与那尊菩萨对望。
她看着他清瘦的面容,看着他微微上翘的、带着一丝悲悯笑意的嘴角,看着他那双仿佛洞悉了世间一切悲苦、却依旧温柔的眼睛。她试图去想象,百年前那位无名的画工,是如何用手中的画笔,将这样一份超越了时间的宁静与慈悲,赋予这冰冷的石头。
然后,她开始动手。
她用了自己所学的全部技艺,也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神。她调配的颜料,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细腻,更加考究。她下的每一笔,都屏息凝神,力求与原作的气韵,融为一体。
在修补菩萨脸颊的肌肤时,她犹豫了很久。
按照传统的法度,佛像肌肤,应用最纯粹的金粉或蛤粉,以示其清净无垢的法身。但阿萦看着那张略显清冷的脸,心中却忽然涌起一个大胆的念头。
她想起了小乙的话:“佛,也是从人修来的。”
她想起了刘大娘脸上温暖的皱纹,想起了“半两食铺龙门店”里那蒸腾的、暖人肺腑的热气。
她觉得,真正的慈悲,不应是高高在上的、冰冷的怜悯。而应是带着温度的、能够感同身受的体恤。
于是,她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甚至可以说是离经叛道的决定。
在她调好的、用上等鱼鳔胶和好的金色颜料里,她悄悄地,只用笔尖,蘸了那么一丝丝,几乎微不可察的、用晕金石磨成的赤金颜料。
她将这两种颜色,在蚌壳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那新的颜色,依旧是华贵的金色,却不再是那种冷冰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纯金。它在金色的基调里,蕴含了一丝极其温暖的、若有若无的赭红。那颜色,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初雪之上,既有雪的纯净,又有光的温暖。
她用这新的颜色,轻轻地、一遍遍地,为菩萨敷上新的面容。
当最后一笔的点绛唇完成时,阿萦退后几步,抬头仰望。
她自己,也呆住了。
石壁上的那尊胁侍菩萨,仿佛活了过来。
他的面容,依旧是清秀的,宁静的。但那份宁静之中,却多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暖和亲近。他的肌肤,在洞口照进来的、柔和的漫射光下,呈现出一种温润如玉的光泽,仿佛有温暖的血液,在其下缓缓流淌。他的眼神,依旧是悲悯的,却不再是遥远的俯瞰,而像是一位温和的长者,在静静地凝视着你,倾听着你心中所有的苦与乐。
他不再只是一尊冰冷的石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他有了一丝“人”的温度。
阿萦知道,自己成功了。
她成功地,将那山下的人间烟火气,化作了山上的佛性光辉。这两者,在她的笔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美的和谐。
她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乙。她想让他看看,她终于做到了。她把那团火,正大光明地,点在了佛的脸上。
' e% _" \' r1 @- u6 S
# _* n0 g; t, y; `0 z; [( B
5 P, |+ t: \+ \' S# f) P# _
作者: xiejin77 时间: 2025-8-16 11:24
拾
8 {# I7 E1 p% C
- y: b, w6 Y# u1 r3 v
1 G9 \- g- o9 }" d1 o6 j$ @: L& x7 A. H& a" [) V* g
几天后,一个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整个龙门山画坊和匠作营。
礼部侍郎裴谏,将于三日后,巡视龙门。
礼部侍郎,从三品大员。对于龙门山上这些最高不过九品的画官石匠来说,简直是天一般的人物。整个龙-门山,都因此陷入了一种紧张而忙碌的氛围之中。所有的工坊,都在进行着最后的清扫和整理。所有的官长,都在反复检查着自己辖下的工程,生怕出一丝一毫的纰漏。
王道玄也变得格外严肃。他把阿萦和其他几个得意弟子叫到身边,反复叮嘱,巡视当日,一定要言行谨慎,不可有半分差池。
阿萦的心中,也有些忐忑。但更多的,是一种隐秘的期盼。
她刚刚完成了自己最得意的作品,那尊胁侍菩萨。她渴望这件作品,能被真正有分量的人看到。礼部侍郎,虽然不是将作监的本管,但位高权重,他的任何一句褒奖,都将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她甚至偷偷地想,如果侍郎大人能称赞一句,那师父的地位,也会更加稳固。而她自己,或许,就能得到更多的自由,去画她想画的东西。
巡视的那天,天色极好。秋高气爽,云淡风轻。
礼部侍郎裴谏的仪仗,在山下列队,旌旗招展,绵延数里。他本人,则在洛阳令、将作监监正等一众地方要员的簇拥下,缓步上山。
裴谏约莫五十岁上下,身形清瘦,面容严肃。他穿着一身绯色的官袍,腰束玉带,顾盼之间,自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他留着三绺打理得一丝不苟的胡须,眼神锐利,像鹰隼一样,扫视着周遭的一切。据说,这位裴侍郎,出身世家,是个有名的经学大家,最是讲究法度,崇尚古风,平生最厌恶的,便是那些不合规矩的、标新立异的东西。
王道玄带着阿萦等一众画工,恭恭敬敬地,在宾阳洞口,列队迎候。
裴谏一行人,在监正大人的引导下,走进了宾阳南洞。洞内,早已点燃了数十支牛油大烛,将石窟照得亮如白昼。
“侍郎大人,请看。”监正大人满面春风,指着那尊阿萦刚刚修补好的胁侍菩萨,语气中充满了自豪,“此尊菩萨,乃北魏遗珍。近日,由本监从九品画官王道玄之徒,阿萦,费时月余,修补完成。此女年岁虽轻,却是天赋异禀,技艺不凡。”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那尊菩萨的身上。
洞内一片寂静。只能听见烛火燃烧时,发出的轻微的“噼啪”声。
阿萦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紧张地绞着自己的衣角,手心里全是汗。她偷偷地,用眼角的余光,去观察裴侍郎的表情。
裴谏站在那尊菩萨像前,一言不发。
他背着手,微微仰着头,眯着眼睛,仔细地端详着。从菩萨的面容,到衣纹的走向,再到色彩的运用。他看得极其仔细,脸上的表情,却没有丝毫变化,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古井。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那沉默,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所有人的心上。监正大人脸上的笑容,渐渐变得有些僵硬。王道玄的额头,也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
终于,裴谏开口了。
他的声音,不高,却冰冷得像山涧里的冬水。
“俗不可耐。”
短短四个字,像四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每个人的心上。
洞内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监正大人脸上的血色,一下子褪得干干净净。“侍郎大人,这……”
“哼。”裴谏冷哼一声,伸出一根手指,直指菩萨的面容,眼神轻蔑而锐利。“佛相,贵在庄严,贵在清净,贵在超凡脱俗,使凡夫俗子见之,心生敬畏,自惭形秽。此乃教化之功,礼法之本!”
他的声音,在石窟里,激起一阵阵回响,震得人耳膜生疼。
“可尔等看这尊菩萨!”他声色俱厉,像是在审判一个罪人,“唇若涂脂,面带桃花,眼含春水!这哪里是悲悯众生的菩萨,分明是取悦凡夫的伶人!看这用色,暖腻阿谀,俗媚入骨!将这佛国净土,弄得一股子市井脂粉气!”
“将作监,掌皇家营造,代天工开物。所出之物,当为天下法式。如今,竟堕落至此!以凡俗之态,污神佛之容,成何体统!简直是……荒唐!败坏!可耻!”
他每说一句,监正大人的腰,就弯下一分。到最后,几乎要躬到地上去。王道玄更是面如死灰,身体摇摇欲坠,若不是身旁的弟子扶着,几乎就要瘫倒在地。
阿萦站在人群的最后,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
她怔怔地看着裴侍郎那张因愤怒而显得有些扭曲的脸,又看了看自己引以为傲的那尊菩萨。
面带桃花?眼含春水?
她在那颜色里,融入的是人间的温暖,是生命的温度。可是在这位大人的眼中,这一切,都变成了轻浮,变成了谄媚。
俗不可耐。
这四个字,像一把最锋利的刀,将她的心,她的梦,她的全部骄傲和信念,都剖开来,碾得粉碎。
她觉得天旋地转,耳边嗡嗡作响,什么也听不见了。她只看见,师父转过头,用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混合着极度失望、愤怒和羞耻的眼神,死死地,盯着她。
那一刻,阿萦觉得,自己从云端,直直地,坠入了最深、最冷的冰窟。
; ^- c/ h1 O" ~' T/ u9 F
3 p6 c4 o6 d% p2 c" W) p1 S
9 j4 v& ]1 h. M
作者: xiejin77 时间: 2025-8-16 19:53
拾壹裴侍郎拂袖而去,留下了一洞的死寂和彻骨的寒意。
监正大人连一句辩解的话都不敢说,只白着一张脸,率领众官吏,诚惶诚恐地,将这位怒气冲冲的贵人送下山去。
宾阳南洞里,只剩下了王道玄和他的几个弟子。
那几十支明亮的牛油大烛,依旧在燃烧着,将那尊被宣判了“死刑”的菩萨,照得纤毫毕现。那温润如玉的肌肤,那悲悯含笑的眼神,在此刻,却像是一个巨大的、无声的讽刺。
王道玄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极度的愤怒和羞辱。他一辈子,都以技艺精湛、严守法度而自傲。今天,却在他最引以为傲的地方,在他最看重的弟子身上,栽了这样一個奇耻大辱的跟头。
他慢慢地转过身,一步一步,走到阿萦的面前。
他的脸色,比洞口的石头还要青。那双平日里总是沉静如水的眼睛,此刻,燃烧着两簇骇人的火焰。
“孽徒!”
他扬起手,一个耳光,狠狠地,扇在了阿萦的脸上。
“啪!”
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石窟里,显得格外刺耳。
阿萦的脸,被打得偏向一边,火辣辣地疼。一缕鲜血,从她的嘴角,慢慢地渗了出來。她却像是感觉不到疼痛,只是怔怔地,看着师父。
“为师是怎么教你的?”王道玄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愤怒而嘶哑,“净手!净心!心无杂念,方能通神!你把为师的话,都当成耳旁风了吗!”
“你从哪里学来这些邪魔外道的东西!啊?是谁教你,用这种……这种淫巧之色,来亵渎佛容的!”
他指着那尊菩萨,手指都在发抖。“你看看你画的好东西!这哪里是菩萨!这分明就是个妖物!你……你把为师的脸,把整个龙门画坊的脸,都丢尽了!”
“师父……”阿萦的嘴唇翕动着,想说些什么。
“住口!”王道玄厉声喝道,“我没有你这样的徒弟!”
他剧烈地喘息着,胸口起伏不定。他闭上眼,似乎是想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但睁开眼时,眼神却更加冰冷,也更加决绝。
“从今日起,”他一字一顿地说,每一个字,都像一块冰,砸在阿萦的心上,“你,再也不是我王道玄的弟子。画坊,也容不下你。你那些‘点绛唇’的活计,全都给我停了!”
“师父!”阿萦身后的几个师姐妹,都忍不住惊呼出声。
停了“点绛唇”的活计,就等于剥夺了一个画工的身份。这对于视画画为生命的阿萦来说,比杀了她还难受。
“你以后,”王道玄看着她,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就去西山那边,看管那些废弃的洞窟。每日打扫,研磨粗料。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再碰画笔!什么时候,你把你心里那些乌七八糟的‘人间烟火’都洗干净了,什么时候,再来见我!”
说完,他再也不看阿萦一眼,转身,踉踉跄跄地,走出了石窟。那背影,在烛光的映照下,显得苍老而佝偻。
阿萦独自一人,还站在原地。
脸上的疼痛,早已麻木。心里,却像被挖空了一个大洞,寒风呼呼地,从里面灌进来。
她慢慢地,抬起头,再次看向那尊她曾引以为傲的菩萨。
那温暖的、悲悯的笑意,此刻在她的眼里,却充满了无尽的悲凉。她以为自己读懂了它,给予了它生命。到头来,却发现,那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她输了。输得一败涂地。
输给了那个高高在上的礼部侍郎,输给了所谓的“法度”和“规矩”,也输给了她最敬爱的师父。
她为之骄傲的、从人间烟火里提炼出的那点温暖,在绝对的权威面前,不堪一击。被轻而易举地,定义成了“凡俗”与“淫媚”。
她慢慢地,沿着石壁,滑坐到地上。
她抱住自己的膝盖,将脸深深地埋进去。
没有哭。
只是觉得,好冷。
龙门山的石头,原来,是没有气味的。它们只有温度。一种能将人从里到外,都冻僵的、亘古的冰冷。
, u/ u8 I! O! ?+ w; ^! M8 \8 U& o- X# G
/ T( Y% G$ G0 R$ j' N; t6 E" v' d; i
* x! ]; V8 [' j* n
作者: xiejin77 时间: 2025-8-17 12:02
拾贰
$ g9 K: @; ?% C" F& U7 A
- t+ m0 o1 W# j+ x0 U西山,是龙门山最偏僻、最荒凉的一角。
这里的洞窟,大多是开凿初期,因为石质不佳,或是工艺不精,而被废弃的。没有宝相庄严的主佛,也没有衣袂飘飘的飞天。只有一些不成形的石胎,和一些被风雨侵蚀得面目全非的残垣断壁。
这里,是龙门山的弃儿。
阿萦,也成了龙门山的弃儿。
她被赶出了东山那间还算齐整的画工厢房,搬到了西山一处破旧的茅屋里。屋子四面漏风,一到晚上,山风呜呜地,像鬼哭。
她每日的工作,就是清扫那些废弃的洞窟,将里面积累了不知多少年的尘土和落叶,一筐筐地背出去。然后,就是研磨最粗劣的石料,给那些刚刚入门的学徒,做练习之用。
她的手,又开始变得粗糙。那双曾经能描绘出最细腻线条的手,如今,每天接触的,是冰冷的扫帚和沉重的石杵。她的指甲缝里,又积满了洗不掉的泥污。
她被禁止碰触任何精细的画笔和颜料。她那只装着所有家当的画箱,被师兄们收走了。连同那卷她视若生命的《神都烟火图》,也一同被锁进了师父的库房。
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沉默的石头。
她不再说话,也不再有任何表情。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麻木地,重复着最枯燥的劳动。
山上的画工石匠们,见到她,都远远地避开,像躲避瘟疫一样。偶尔有几个相熟的师姐妹,会偷偷地来看她,给她送些吃食,看着她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也只能叹着气,掉几滴眼泪,却不敢多说什么。
阿萦的世界,又变回了五年前。不,比五年前,还要孤独。五年前,她一无所有,所以无所畏惧。而现在,她是从云端跌落,品尝过温暖和希望,再被打回原形。那种从内到外的剥夺感,更让人绝望。
她不知道这样过了多久。十天,还是一个月,还是一年。她对时间,已经失去了概念。
她以为,自己会就这样,在这片废弃的石窟里,慢慢地,风化成一尊没有面目的石像。
直到那天傍晚。
她清扫完最后一个洞窟,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在回茅屋的山路上。夕阳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孤单。
远远地,她看见自己那破旧的茅屋前,站着一个人。
一个穿着蓝色短衫的、熟悉的身影。
阿萦的心,猛地一颤,脚步,下意识地停住了。
是小乙。
他就站在那里,背靠着一棵枯树,嘴里叼着一根草茎。夕阳的余晖,照在他身上,将他的身影,染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
他看见了她,脸上没有了往日的嬉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阿萦站在原地,没有动。她不想让他看见自己现在这副狼狈的样子。她穿着一身沾满灰尘的、破旧的粗布衣裳,头发用一根布条胡乱地挽着,脸色苍白,嘴唇干裂。像一朵被霜打蔫了的花。
她低下头,转身想走。
“阿萦!”
小乙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不是喊,更像是一种笃定的陈述。
阿萦的脚步,像被钉在了地上,再也无法移动分毫。
他几步就走到了她的面前。他看着她,那双黑亮的眼睛里,盛满了她看不懂的情绪。有心疼,有愤怒,还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深沉的温柔。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伸出手,轻轻地,用他那带着薄茧的、粗糙的指腹,拂去她脸颊上的一片落叶。
他的触碰,很轻,却像一道电流,让阿萦死寂的身体,猛地一颤。
眼泪,就那么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
这段日子里,她所承受的所有委屈、不甘、绝望和孤独,都像决了堤的洪水,在这一刻,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她咬着嘴唇,不想让自己哭出声,可那泪水,却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止不住。
“哭吧。”小乙的声音,很轻,很柔,“哭出来,就好了。”
阿萦终于再也忍不住,蹲下身,将脸埋在膝盖里,放声大哭起来。那哭声,压抑了太久,嘶哑,破碎,像一只受伤的小兽,在绝望地悲鸣。
小乙就在她身边,默默地蹲下,什么也没做,只是将自己的肩膀,轻轻地,靠在了她的身边。
他没有说“别哭了”这样的废话,也没有说“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样空洞的安慰。他只是用自己的存在,给了她一个可以放肆哭泣的、安全的角落。
夕阳渐渐沉没,暮色四合。山风变得清冷。
不知哭了多久,阿萦的哭声,才渐渐止住。变成了低低的、委屈的抽噎。
“那些当官的,”小乙的声音,在寂静的山谷里,清晰地响起,“都是睁眼瞎。”
阿萦抬起那张泪痕交错的脸,怔怔地看着他。
“他们懂个屁的画。”小乙的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辛辣的嘲讽,“他们看的不是画,是规矩,是官威。一幅画,在他们眼里,跟一份呈上去的公文,没什么两样。字写得不对,格式不对,就是错的。至于那字里行间的意思,是好是坏,他们根本不在乎,也看不懂。”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递到阿萦面前。
那是一块小小的、用手帕包着的胡饼。还是热的。是“静心斋”隔壁,张二哥家的。
“吃点东西吧。”他说,“老王让我给你带的。他说,天大的事,也得先填饱肚子。肚子暖了,心,才不会那么冷。”
阿萦看着那块胡饼,又看了看小乙。
“我听说了。”小乙说,眼神变得深沉,“我去找过你师父。”
阿萦的心,猛地一紧。
“我跟他吵了一架。”小乙自嘲地笑了笑,“没什么用。他那个人,脑子里装的全是条条框框,比我铺子里最硬的石头,还顽固。我跟他说,你的画,是活的。他说,活的东西,就容易越界。”
“他说……他是在保护你。”
“保护我?”阿萦惨然一笑,声音沙哑,“他把我关进这座笼子里,就是保护我?”
“是啊。”小乙点了点头,眼神复杂,“他说,这个世道,容不下太扎眼的东西。今天,是一个侍郎大人说你俗。明天,就可能是皇帝说你妖。到时候,掉的,就不只是饭碗,是脑袋了。他说他把你打到谷底,是为了让你学会,怎么把自己藏起来。”
阿萦沉默了。她想起师父当年,把自己从饥民堆里捡回来时,那双清亮的眼睛。或许,师父的内心,比她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可我觉得,他是错的。”小乙的声音,又变得坚定起来,“人活一辈子,要是不能痛痛快快地做自己,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有才华,就该亮出来。有火,就该烧起来。怕这怕那,畏首畏尾,那不叫活着,那叫熬着。”
他站起身,朝着山下那片已经亮起万家灯火的神都,伸出手臂。
“阿萦,你看。”
阿萦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山下的洛阳城,在暮色中,像一片璀璨的星海。每一點灯火,都代表一个家庭,一个故事。那里面,有欢笑,有哭泣,有争吵,有温情。有无数个像老王、像刘大娘一样的、活生生的人。
“他们,才是你的画,真正的知音。”小乙的声音,像洪钟一样,在阿萦的心里敲响,“那个姓裴的侍郎,他算老几?他一百年后,就是一捧黄土。可你的画,只要还在,就会有人看懂。会有人,从你画里,看到这片土地的温度,看到这些人的喜怒哀乐。这,才是真正能传下去的东西。”
“你的笔,没有错。你的心,更没有错。错的,是这个不许人说真话的世道。”
他转过头,看着阿萦,那双丹凤眼里,燃烧着两簇比星辰还要明亮的火焰。
“阿萦,你想不想,再把笔拿起来?”
阿萦的心,被这句话,狠狠地,撞了一下。
再把笔拿起来?
她还有机会吗?
她看着自己的手,那双粗糙的、沾满泥污的手。她还能画吗?
仿佛看穿了她的犹豫,小乙笑了。他从身后那个一直背着的、半旧的布包里,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卷素绫。
还有一只小小的木盒。
阿萦的呼吸,瞬间停止了。
那正是她被收走的那卷《神都烟火图》,和她用全部积蓄换来的那只,装着晕金石颜料的盒子。
3 y' a" Z. K- V: k2 a( q5 \9 {
; u* k1 x2 @; {( y, A6 H- e
8 ?4 y1 b6 @* v- N
作者: xiejin77 时间: 2025-8-18 07:23
拾叁% i6 H3 S0 h0 U3 K5 ~+ d
3 c( P9 V1 r, ^/ Y
) K& {! n% W% H$ D
; q+ d: L: T- C" |" B! t
- |5 y9 F1 ^" r d; ?% G Y, L
/ C; \+ W9 h) @' r7 C" I3 K+ R小乙手里,是那卷素绫,和那个木盒。
在沉沉的暮色里,它们像两块从深水里捞起的石头,沉默,却有着惊人的重量。
阿萦的呼吸凝滞了。她怔怔地看着那两样曾被她视若生命、如今却像是在嘲讽她一般回到手中的东西。她的画,她的颜料,她那个天真而炽热的梦,如今都已成了一个笑话,一个被权威轻蔑地踩在脚下、碾得粉碎的笑话。
“拿走。”她的声音沙哑,像是从喉咙深处撕扯出来的,带着血腥气,“我不要了。这些东西……都死了。”
“胡说。”小乙的回答,简洁而有力。他走到阿萦面前,不容分说地,将画卷和木盒,塞进了她的怀里。“东西是死的,还是活的,不看东西本身,看用它的人。你心死了,它才是死的。”
那木盒的边角,硌得她胸口生疼。那熟悉的重量,却像一块烙铁,烫得她浑身一颤。
她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他:“我的心……早就死了。从那位侍郎大人说出‘俗不可耐’四个字的时候,从师父打我那一巴掌、收走我画笔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我画的那些人,那些烟火气,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些上不了台面的、污秽的东西。我……我错了,小乙,我真的错了。”
“你没错。”小乙蹲下身,与她平视。他的眼神,在愈发浓重的夜色里,亮得惊人,像两簇顽固燃烧的野火。“阿萦,你抬头看看。”
阿萦下意识地顺着他的目光,望向山下。
洛阳城已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在暮色中连成一片璀璨的光海,温暖,喧嚣,充满了生命力。伊水像一条黑色的绸带,静静地流淌,将这片光的海洋,映照出一个同样璀璨的倒影。
“你告诉我,”小乙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奇特的、能安抚人心的力量,“是山上那些冰冷的石头好看,还是山下这片温暖的灯火好看?”
这个问题,阿萦无法回答。
过去,她会觉得,都好看。一种是清净的、永恒的美;一种是喧嚣的、短暂的美。她贪恋后者,却又敬畏前者,因此活得分裂而痛苦。
“如果,”小乙仿佛看穿了她的内心,一字一句地说,“非要选一个呢?”
阿萦的嘴唇翕动着。她看着那片灯海,想起了“半两食铺龙门店”里那碗能烫暖五脏六腑的羊肉汤,想起了刘大娘那张布满皱纹的、和蔼的笑脸,想起了那些为生计而搏命的纤夫,他们粗砺的皮肤上,闪烁着比金粉更耀眼的汗水的光芒。
她的心,像被一只温柔的手,轻轻地拨动了一下。
“……灯火。”她轻声说,声音细若蚊蚋,却无比清晰。
说出这两个字,她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又像是卸下了一个沉重了许多年的枷锁。
小乙笑了。那笑容,在夜色中,爽朗而温暖。
“这不就结了?”他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你喜欢灯火,你就去画灯火。你心里装着那些活生生的人,你就把他们画出来。画给那些同样活在灯火里的人看,画给那些能看懂你画里那碗羊肉汤有多烫、那个胡饼有多香的人看。至于山上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官老爷,他们爱懂不懂,关你屁事?”
最后那句粗话,说得直白而痛快,像一块石头,砸碎了阿萦心中那面名为“规矩”与“敬畏”的冰墙。
她怔怔地看着小乙,忽然觉得,自己一直以来,都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她总想着,要让山上的人,认可山下的美。她想向师父证明,人间烟火亦可入画,亦有神性。她想得到那个权威的、来自上层的肯定。
可她从未想过,山下的美,根本不需要山上的认可。
灯火,从来都不是为了照亮星辰而燃烧的。它只是为了温暖那些在夜路里赶回家的人。
“可是……”阿萦的眼中,依旧有着犹豫和迷茫,“我还能画什么?那幅《神都烟火图》,已经被我的怯懦和妥协玷污了。我那时候,还想着……想着把人间气,藏在佛性里,偷偷地渡过去。结果,两边都不讨好。”
“那就扔了它。”小乙说得轻描淡写。
阿萦一惊:“扔了?”
“对,扔了。”小乙点点头,眼神却无比认真。“既然是偷偷摸摸的,那就说明你心里还是虚的,还是怕的。你怕你师父,怕那些规矩。你画出来的东西,自然也带着一股子小家子气。要画,就堂堂正正地画。不藏,不掖,把你心里那团火,痛痛快快地点起来,烧给全天下人看!”
他看着阿萦,那双丹凤眼里,闪烁着一种近乎疯狂的、灼热的光芒:“阿萦,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
“赌什么?”
“赌这神都城里,到底是睁眼瞎多,还是心里亮堂的人多。”小乙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我们重新画一幅。不画在那娇贵的素绫上,那玩意儿是给文人雅士附庸风雅用的。我们画在一张更大的、更结实的、不怕风吹雨打的东西上。画完了,咱们不藏着掖着,就把它挂在‘静心斋’那棵大槐树底下!让南来北往的人都看看,让那些喝羊肉汤的、卖豆腐的、拉大船的都看看,看看你画的,到底是不是他们自个儿的日子!”
阿萦的心,被他这番话,说得热血沸腾。
把画挂在市集上?
那简直是……她从未敢想象过的事情。她的画,从来都是藏在箱底的私密,或是供奉在石窟里的仰望。她从未想过,有一天,它们可以就那么坦然地,暴露在最嘈杂的、最世俗的阳光之下。
“我……”她还是不敢,“我没有地方画。在山上,我连笔都不能碰了。”
“谁说要在山上画?”小乙笑了,那笑容里带着几分神秘和笃定,“跟我走。我给你找个地方。一个全神都烟火气最足的‘画室’。”
! u5 W! D# D9 f( c! p* d# | F. C
2 j- \- H, [( Q1 c. v8 F# Y
作者: xiejin77 时间: 2025-8-19 08:00
拾肆. T% Q1 c8 M( I4 s* s
, B2 k- s/ ~. o2 }" ^+ N% C
J" E# o6 b4 U/ A$ J8 Q. c5 J- Z9 x
小乙口中那个“烟火气最足的画室”,竟然就是“半两食铺龙门店”的后院。
穿过那个人声鼎沸、热气蒸腾的堂屋,绕过那口永远咕嘟咕嘟冒着香气的大汤锅,掀开一道半旧的蓝布帘子,后面就是一个不大的、堆满了杂物的小院。院子里,靠墙码着半人高的劈柴,角落里扔着几个空酒瓮,还有一架用来晾晒干菜的竹梯。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复杂而安逸的味道:羊汤的浓香、劈柴的木香、还有泥土和阳光的气息。
院子尽头,有一间小小的、勉强能称之为屋子的厢房。那屋子,原本是老王用来堆放杂粮和备用桌凳的仓库。
当小乙领着阿萦,第一次站在这间所谓的“画室”里时,阿萦几乎有些哭笑不得。
屋子很小,光线昏暗,只有一扇小小的、糊着油纸的窗户。墙角结着蛛网,地上积着一层薄薄的灰尘。与其说是画室,不如说是一个被人遗忘了的储藏间。
“就这里?”阿萦环顾四周,眼中满是怀疑。
“就这里。”小乙却显得兴致勃勃。他像一阵风似的,把屋里的杂物三下五除二地搬了出去,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破扫帚,呼呼喝喝地,将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他又变戏法似的,从后门拖进来一张巨大而厚实的旧门板,用两条长凳架起来,成了一张宽大的、足以铺开巨幅画卷的画案。
做完这一切,他拍了拍手上的灰,额上沁出了一层薄汗,脸上却是心满意足的笑容:“怎么样?收拾一下,不也挺像回事儿?”
阿萦看着他忙碌的身影,看着他那件被汗水浸湿了后背的蓝色短衫,心里某个地方,被一种温热的东西,悄悄地填满了。
正在这时,一个身影,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东西,掀开帘子走了进来。
来人是个五十岁上下的妇人,身形微胖,穿着一身干净的粗布衣裳,腰间系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围裙。她的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整齐的发髻,脸上布满了岁月留下的皱纹,但那双眼睛,却和善而明亮,带着一种洞悉世情的、温暖的智慧。
这便是“半两食铺龙门店”如今真正的主心骨,王大娘。也是小乙口中那个“比谁都懂道理”的人。
老王就是那个憨厚实在的胖大叔,孟津白鹤镇铁谢村人,安排的一手好汤水。三年前,因为王大娘积劳成疾,到神都求医;阴差阳错的盘缠耗尽还欠了利钱,带着王大娘困在积善坊中。半两食铺以韦掌柜为首的众人搭救脱难。老王带着王大娘不敢还乡,只能在这洛南的龙门半是感恩半是借名,顶着半两食铺龙门店的招牌开了生意糊口。没曾想,王大娘的身体好起来不久,老王却急病而去。这家铺子原本是她和她丈夫老王一起开的。所有人都以为,这间小小的食铺,怕是开不下去了。没想到,王大娘一个人,硬是把这铺子撑了下来。汤,还是老王留下的方子,每日天不亮就起来熬。待客,比老王在时,更多了几分女人的细致和温情。来吃汤的,还是那些熟客。他们敬重这位坚韧的妇人,都尊称她一声“大娘”。久而久之,这间食铺,反倒比从前,更像一个家了。
“小乙,你这孩子,又瞎折腾什么呢?”王大娘的声音,洪亮而爽利,带着一种母亲般的嗔怪,“这位就是阿萦姑娘吧?快,快坐下,喝碗热汤暖暖身子。瞧这小脸白的,在山上受委屈了吧?”
她不由分说地,将手里的汤碗,塞进了阿萦的手中。那是一碗新熬好的羊肉汤,汤色奶白,上面只撒了几粒翠绿的葱花,没有放任何辛辣的调料,温润醇厚,最是养人。
阿萦捧着那碗温热的汤,看着眼前这位素未谋面、却亲切得像是认识了许久的妇人,眼眶一热,险些又掉下泪来。
“大娘……”
“哎,什么都别说。”王大娘摆了摆手,在那张临时搭成的“画案”边坐下,看着小乙,眼神里满是慈爱,“这小子,都跟我说了。他说,有个天仙一样的姑娘,画的画,能把人的魂儿都勾走,却被一帮有眼无珠的官老爷给欺负了。他要帮这姑娘,讨个公道。”
她转过头,看着阿萦,那双明亮的眼睛,像是在端详自家的女儿:“姑娘,大娘我没读过书,不懂什么叫画。但我知道一个理儿,能把咱们这些老百姓的日子,画得活灵活现的,那就是好画。别怕,你想画什么,就在这儿画。有大娘在,天塌不下来。谁敢来找你麻烦,先问问我手里这把汤勺答不答应!”
说着,她扬了扬手中那把用了多年、被磨得油光发亮的、沉甸甸的大铁勺,自有一股不容置疑的气势。
阿萦的心,彻底地,被这碗汤,和这番话,暖透了。
从那一天起,这间堆满了柴火和杂物的后院,就成了阿萦的秘密基地。
而小乙,也真的给她弄来了一张巨大的、他口中“不怕风吹雨打”的画布。那是一张旧的船帆。不知是从哪艘退役的货船上拆下来的。帆布质地粗糙,厚实,带着一股子被河水浸泡、被日光暴晒后留下的、独特的咸腥味和岁月感。上面甚至还有一些修补过的、深色的补丁和磨损的痕迹。
“这玩意儿,比那什么素绫,结实多了。”小乙得意地说,“它自己身上,就带着故事。”
阿萦抚摸着那张粗糙的帆布,感受着它凹凸不平的肌理。她忽然觉得,小乙说得对。这样一张历经了风浪的帆布,才是承载这人间烟火,最合适的载体。
她没有再画之前那幅《神都烟火图》。
她要画一幅全新的。
这一次,她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偷偷摸摸的记录者。她就生活在这烟火气的中心。
每天清晨,她被食铺里传来的第一阵剁肉声唤醒。白天,她就在那间小小的厢房里作画。画案上,铺着巨大的帆布。她的颜料碟,就摆在旁边。那块晕金石,被她重新取出,这一次,她心中再无杂念。她想着王大娘熬汤时那专注的神情,想着小乙为她搭画案时那额上的汗水,想着门外那些食客们热闹的呼噜声。她手下的石杵,变得沉稳而有力。
她磨出的赤金颜料,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而厚重的光泽。那光泽,不再是神佛脸上那清冷的、高高在上的金光,而是带着人间温度的、夕阳一般的光辉。
她画画的时候,不再屏息凝神,如履薄冰。她可以听见院子里王大娘和邻居们的说笑声,可以闻到从堂屋飘来的、霸道的羊汤香气。有时候,小乙会端一碗刚做好的饭菜进来,不由分说地按她坐下,看着她吃完,才许她继续画。他们的对话,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今天码头上又来了艘大船,从江南运来的丝绸,那颜色,啧啧,跟天上的云霞似的。”
“隔壁张二哥家的胡饼,今天又涨价了,一个要多加一文钱。”
“听说了吗?城西那个耍猴的老头,他那只老猴子,学会给人算命了,准得很。”
阿萦一边听着,一边画着。她把这些琐碎的、鲜活的、带着生活温度的一切,都揉进了自己的笔墨里。
她的画室,也渐渐地,不再是她一个人的秘密。
那些来食铺吃汤的熟客们,都知道了后院里,住着一位会画画的“神仙姑娘”。他们好奇,却又不敢轻易打扰。只是偶尔,会从门帘的缝隙里,偷偷地朝里张望。
第一个走进来的,是那个总在码头拉货的、名叫“铁牛”的壮汉。他那天多喝了两碗酒,胆子大了些,端着汤碗就闯了进来。他本想看看热闹,却在看到那幅巨大的画时,愣住了。
阿萦正在画伊水边的纤夫。画中,一个赤裸着上身、肌肉虬结的汉子,正弓着背,将一根粗大的纤绳,深深地勒进自己的肩胛。他的脸,被风霜刻满了沟壑,牙关紧咬,额上青筋毕露。那是一种与命运搏斗时,最原始、最顽固的姿态。
铁牛看着那画中的人,看着那熟悉的纤绳和码头,眼眶,竟慢慢地红了。
“这……这不是老周吗?”他喃喃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去年冬天,为了多挣几个钱给娃儿买件新衣裳,掉进冰窟窿里,没上来那个……”
阿萦停下了笔。她看着这个满脸横肉、一身酒气的壮汉,此刻脸上那悲伤而怀念的神情,心中一动。
从那天起,这间小小的画室,变得热闹了起来。
越来越多的人,会端着碗,好奇地走进来。他们在阿萦的画布上,寻找着自己熟悉的身影。
“哎呀!这不是东街卖豆腐的孙寡妇吗?瞧这眉眼,一模一样!”
“大娘,您快看,姑娘把您熬汤的样子也画上去了!真神了!”
“小乙哥,你看,这不是你吗?躲在槐树底下偷懒的样子!”
他们成了阿萦最好的模特,也是她最真诚的观众。他们会告诉她,那个补鞋匠的背,应该再驼一点;那个卖花女的篮子里,春天应该是牡丹,秋天就该是菊花了。他们还会给她带来各种各样的东西,一篮刚摘的鲜果,几条新钓的活鱼,或是一块刚出炉的、热气腾腾的炊饼。
阿萦的画,就在这片嘈杂、温暖、充满了人情味的烟火气中,一点点地,生长起来。它像一棵树,根,深深地扎进了这片土地;枝叶,则吸取着这最真实的人间气,舒展,繁茂。
她画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自由。
她用最粗犷的线条,去勾勒那些纤夫和石匠饱经风霜的轮廓。又用最细腻的笔触,去描绘孩童脸上那柔软的、吹弹可破的肌肤。
她用那珍贵的晕金石颜料,毫不吝惜地,去渲染夕阳下每一片瓦片的余晖,去点缀老王家汤锅里升腾的、金色的热气,去描画每一个劳作者身上,那被汗水浸润后,在阳光下闪烁的、健康的光泽。
那金色,不再冰冷,不再神圣。它属于人间,属于每一个在尘世中努力活着的、平凡的生命。
而小乙,始终是她最沉默,也最坚实的守护者。
他会在她颜料用尽时,跑遍全城,为她寻来最好的石青和藤黄。他会在她疲惫时,不由分说地夺下她的画笔,拉着她去集市上听一场热闹的百戏。他会默默地,修好她那间漏风的屋顶,为她那张冰冷的床铺,换上一床温暖的新棉被。
他从不说什么甜言蜜语,也从不问她,画这幅画,将来要如何。
他只是用他的方式,为她撑起了一片,可以让她安心沉浸、自由呼吸的天地。
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像王大娘那锅文火慢炖的汤。没有惊心动魄的开始,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相伴中,在无数个共享的、盛着羊肉汤的黄昏里,将彼此的味道,一点点地,熬进了自己的生命。那滋味,醇厚,绵长,暖到骨子里去。
秋去冬来,春暖花开。
整整一年的时间,那张巨大的、承载了无数人故事的船帆,终于被色彩和生命,彻底填满。
+ B' u1 H% ]6 T: o
( Y3 R; n5 ?4 C. C
, r8 _/ q0 O/ C0 B
作者: xiejin77 时间: 2025-8-20 07:55
拾伍4 T& l H" d u. X0 T8 e/ r& b
8 ?0 y8 `9 t5 O* n2 I' y
- }( V- X! G4 E7 _1 B
, _. R9 E" \& }+ p$ ]神龙二年的仲夏,洛阳城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百工节”。
这节日源于何时,已不可考。只知每逢此时,来自天南地北的能工巧匠,都会汇集于此,在洛水之畔的南市,将自己最得意的作品,陈列出来,一较高下。小到一只精巧的玉佩,大到一架繁复的水车,凡是靠手艺吃饭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荣光。
这一天,整个南市,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比上元灯节还要热闹。
而在“静心斋”市集入口那棵最显眼的大槐树下,一幅前所未见的巨画,迎风招展,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那幅画,就挂在小乙的铺子门前。画的,正是这片他们朝夕相处的、活色生香的市井。
画的尺幅极大,几乎有两丈长,一丈高。画的载体,不是娇贵的素绫,而是一张粗糙厚实的旧船帆。画的内容,更是包罗万象,气象万千。
画的中心,是那口永远热气腾腾的大汤锅。“半两食铺龙门店”的老板娘王大娘,正围着围裙,满面红光地笑着,用一把大勺,搅动着满锅奶白的浓汤。那汤的热气,被画家用一种温暖的、流动的赤金色细细渲染,氤氲升腾,几乎要从画里飘散出来,带着一股子暖人肺腑的香气。
围绕着汤锅的,是数不清的人物。有埋头喝汤的脚夫,有光着膀子划拳的船工,有在码头上扛着沉重货包的苦力,有在伊水边捶洗衣物的妇人。再往远处,是修补佛像的石匠,是捏糖人的老汉,是街角斗鸡的闲人,是追逐打闹的孩童……
画中每一个人,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他们的衣衫或许破旧,面容或许粗糙,但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一种顽强的、生机勃勃的光。画家更是用一种近乎奢侈的方式,将那温暖的赤金色,洒遍了画面的每一个角落。洒在纤夫古铜色的脊背上,洒在妇人沾湿的发梢上,洒在孩童红扑扑的脸蛋上,洒在每一个平凡而劳碌的身影之上。
那金色,不是佛光,却比佛光,更有人间的温度。
这幅画,没有名字。或者说,它不需要名字。
每一个站在画前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或自己身边人的影子。
“哎呀!这……这不是我吗?”一个卖菜的婆婆,指着画中一个蹲在菜摊后、数着铜钱的妇人,惊喜地叫了起来,“天呐,连我头上那根裂了纹的木簪子,都画出来了!”
“快看!那是铁牛哥!他正跟人掰腕子呢!瞧那胳膊,青筋都爆出来了!”
“这……这不是小乙吗?这小子,又躲在人家铺子后头打瞌睡!”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惊叹和善意的哄笑。这幅画,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件需要仰望的艺术品。它就是他们的生活,是他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的、琐碎而真实的日子。
阿萦和小乙,还有王大娘,就站在人群的后面,静静地看着。
阿萦的心,从未像此刻这样,跳得如此剧烈。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一种巨大的、潮水般的感动。她看到那些平日里为了生计而奔波劳碌的人们,在她的画前,露出了那样纯粹的、发自内心的笑容。那一刻,她觉得,自己这一年来的所有辛苦和坚持,都有了意义。
她偷偷地,看了一眼身旁的小乙。他也正看着她,那双黑亮的丹凤眼里,盛满了温柔的笑意和毫不掩饰的骄傲。他朝她,悄悄地,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阿萦的脸,微微一红,心里却甜得像灌了蜜。
正在这时,人群忽然一阵骚动,像是潮水一般,向两侧分开,让出了一条通道。
一队身着绯色官袍、前呼后拥的官员,正朝着这边,缓步走来。为首的一人,约莫五十出头,身形清瘦,面容严肃,三绺胡须打理得一丝不苟。正是时隔一年,恰好又来此地巡视的礼部侍郎,裴谏。
阿萦的心,猛地一沉。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在这一瞬间,凝固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再次遇到这个曾将她的尊严和梦想,彻底击碎的人。
裴谏本只是例行巡视,却被前方那不同寻常的喧闹所吸引。他皱着眉,拨开人群,一眼,就看到了那幅挂在大槐树下的巨画。
当他的目光,落在画上的那一刻,他先是微微一愣,随即,那张严肃的脸,迅速地阴沉了下来。那眼神,变得像一年前在宾阳洞中那样,锐利,冰冷,充满了轻蔑和厌恶。
“哼!”他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哼,声音不大,却让周遭的喧闹,瞬间平息了下来。“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将如此……如此鄙俗不堪之物,悬于闹市!成何体统!”
他指着那幅画,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怒火:“奇技淫巧,哗众取宠!画些引车卖浆之流,乱哄哄,脏兮兮,毫无章法,毫无美感!将这煌煌神都,画得如同一处藏污纳垢的贫民窟!这不仅是在玷污艺术,更是在……在藐视朝廷,丑化圣朝气象!”
他的声音,一句比一句严厉,像一把鞭子,抽在空气里。周围的百姓们,被他这通官威十足的训斥,吓得噤若寒蝉,一个个低下了头,不敢作声。
“来人!”裴谏厉声喝道,“把这伤风败俗的画,给本官……摘下来,烧了!”
他身后的几个侍卫,应声而出,手按腰刀,就要上前。
阿萦的脸色,煞白如纸。她下意识地想冲上去,却被小乙一把拉住。小乙对她摇了摇头,眼神却异常镇定。
就在那几个侍卫即将碰到画卷的瞬间,一个身影,挡在了他们面前。
是王大娘。
她依旧穿着那身粗布围裙,手里,还拿着那把油光发亮的大汤勺。她没有看那几个气势汹汹的侍卫,而是直直地,看着那位高高在上的礼部侍郎。她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畏惧,只有一种母亲般的、不容侵犯的平静。
“侍郎大人,”她的声音,洪亮而清晰,响彻在每一个人的耳边,“您说这画鄙俗,说它丑化神都。可民妇不明白,这画上,哪一点,是假的?”
她伸出那把汤勺,指向画的中心,那个笑得满面红光的妇人。
“那是我。”她说,语气平静而笃定,“我丈夫死了,我一个女人家,靠着这口汤锅,养活自己,也让那些干了一天活的苦哈哈们,能喝上一口热汤。我不偷不抢,靠力气吃饭。大人,这很鄙俗吗?”
她又指向那个在码头上扛着货包、汗流浹背的汉子。
“那是城南的刘三,家里有八十岁的老娘,和三个等着吃饭的娃。他一个人,扛着全家的日子。前几天,他扛包闪了腰,现在还躺在家里。大人,这很丑陋吗?”
她再指向那个抱着孩子的、满脸慈爱的妇人。
“那是东市的吴嫂,她男人去年修河堤,被石头砸死了。她一边给人洗衣,一边带着孩子。孩子前几天病了,她半夜抱着孩子,跑了三家药铺。大人,这很伤风败俗吗?”
王大娘的声音,一句句,一声声,像锤子一样,敲在每个人的心上。她没有说任何大道理,她只是在讲述,讲述这画里每一个人物,背后那最真实、最平凡的故事。
“大人,”她最后说,眼中闪烁着泪光,却无比坚定,“这画上的人,他们不体面,不富贵。他们流汗,他们吃苦,他们为了活着,拼尽了力气。他们,就是这神都的根,是这座城的骨头!您把他们都烧了,这神都,还剩下什么?就剩下你们这些干干净净的官老爷,和山上那些不会说话的石头菩萨了吗?”
一番话,掷地有声。
裴谏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来反驳,却发现,自己竟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可以斥责艺术的“法度”,可以批判美学的“格调”,但他无法反驳这些活生生的、带着血泪和温度的真实。
而就在这时,人群中,一个又一个的人,站了出来。
“大人,那画上是我!我就是那个补鞋的!”
“那是我婆娘!她就是这么笑的!”
“不许烧!谁敢动这画,先从我身上踩过去!”
那些画中的人,画外的人,那些引车卖浆者流,那些贩夫走卒,在此刻,都挺起了胸膛。他们一个个,自发地,走上前,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在画前,组成了一道沉默而坚固的、血肉的城墙。
他们没有武器,没有官威。他们只有自己那卑微而真实的生命,和那份对共同记忆的守护。
那几个侍卫,手握着刀柄,却再也无法上前一步。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一幅画,而是整座活着的、会呼吸、有温度的神都。
裴谏站在那里,被这道人墙,和墙后那幅色彩斑斓的画,映衬得无比孤单,也无比苍白。他引以为傲的权威、法度、规矩,在这面由无数凡人组成的、最质朴的墙面前,不堪一击。
他终于明白了。他可以烧掉一张帆布,却烧不掉这人世间最顽固的、生生不息的烟火。
他看着那幅画,看着画中那些他曾不屑一顾的面容,那温暖的、充满生命力的赤金色,在此刻,竟有些刺痛他的眼睛。他似乎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坚守了一生的那些信念。
许久,他挥了挥手,那动作,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
“……我们走。”
他转过身,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狼狈地,几乎是落荒而逃般地,离开了这个不属于他的、太过真实的人间。
. B2 i& u r4 F8 c
7 f$ R5 m$ H% j, G2 ]7 J
0 y4 A( U% [ y0 M# b* X9 g% A
作者: xiejin77 时间: 2025-8-21 08:27
拾陆7 z$ v0 U. O' P
1 u# b; t% a* R
. k" c Q$ Y' ^% \+ x1 p3 S
" A4 B4 ]2 v2 p) x( v裴侍郎走了。
他身后那道由普通百姓组成的“人墙”,却没有立刻散去。他们依旧默默地站着,守护着那幅属于他们自己的画。直到那队绯色官袍的背影,彻底消失在街角,人群中,才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劫后余生般的欢呼。
王大娘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腿一软,险些坐倒在地,被身旁的几个妇人七手八脚地扶住。她刚才看似镇定,其实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
而阿萦,早已泪流满面。
那不是委屈的泪,也不是恐惧的泪,而是一种被巨大的幸福和感动包裹的、温热的泪水。她看着眼前这些可爱的、勇敢的人们,看着他们脸上那质朴而真诚的笑容。这一刻,她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画家。
她挣脱小乙的手,冲进人群,和王大娘,和那些她画过的、也守护了她的画的人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一日,成了“静心斋”市集一个不成文的节日。
那幅被命名为《神都烟火图》的巨画,没有被收起来。在所有人的坚持下,它就那么一直挂在大槐树下,成了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每日,都有无数人,专程从城里各处赶来,只为看一看这幅“会说话”的画。
他们在画上寻找自己,寻找亲人,寻找邻里。他们对着画,指指点点,开怀大笑,或是默然垂泪。这幅画,不再仅仅是一幅画,它成了一面镜子,一面墙,一个纪念碑。映照着,承载着,也纪念着,这座城市里,最真实的生命和情感。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当市集早已散去,万籁俱寂之时,一个苍老的身影,独自一人,悄然来到了大槐树下。
是王道玄。
他穿着一身深色的便服,隐在槐树巨大的阴影里,久久地,凝视着那幅在月光下依旧色彩斑斓的画。
他来过很多次了。白天,他混在人群里,听着那些百姓对画的评说。夜晚,他一个人来,静静地看。
他看着那画,看着那粗糙的、满是补丁的船帆,看着那大胆的、甚至有些“野”的笔触,看着那被他曾经斥为“淫巧”的、温暖的赤金色,洒遍了每一个卑微的角落。
他看到了那个满面红光、正在熬汤的王大娘,从她慈和的眼神里,他仿佛看到了宾阳洞里那尊胁侍菩萨悲悯的笑意。
他看到了那个弓着背、与命运搏斗的纤夫,从他虬结的肌肉和紧咬的牙关里,他仿佛看到了潜溪寺里那些金刚力士愤怒的力量。
他看到了画中所有的人。他们哭,他们笑,他们劳作,他们挣扎。他们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凡人”。可将这千百万的“凡人”汇聚在一起,那种生生不息的、顽强的生命力,那种在苦难中依旧能迸发出的温情与坚韧,不也正是佛法所说的“众生相”,不也正是那最高境界的“慈悲”吗?
他忽然明白了。
他一辈子,都在教弟子“净手、净心”,追求那至纯至净的佛国。他让阿萦远离人间,是怕那红尘的烟火,污了她手中的笔,和心中的佛。
可他错了。
真正的佛,从来就不在九天之上,不在那清冷的、一尘不染的石窟里。
佛,就在这人间。
在这一碗滚烫的汤里,在这一身淋漓的汗里,在这一份最质朴的、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里。
阿萦没有走火入魔。她只是用她的笔,找到了那条,从人间,通往佛国的、真正的路。
而他自己,那个守着法度、守着规矩、守了一辈子的王道玄,却差点成了一个画地为牢的、真正的睁眼瞎。
他看着那幅画,老泪纵横。
第二天一早,阿萦正在后院帮王大娘收拾碗筷,小乙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阿萦!你师父来了!”
阿萦心头一紧,手里的碗,险些掉在地上。
她走出后院,看到王道玄,就站在“半两食铺龙门店”的门口。他换上了那身熟悉的青色官服,身形依旧清瘦,背却仿佛比从前更驼了一些。他没有走进来,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个充满了油烟气和喧闹声的小铺子。
阿萦走到他面前,低下头,轻轻地叫了一声:“师父。”
王道玄看着她。看着她身上那件浆洗得干干净净的粗布衣裳,看着她那双不再纤细、却依旧稳静的手,看着她那张在人间烟火的熏陶下,变得比从前更加生动、也更加宁静的脸。
他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愧疚,有欣慰,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释然。
他没有说任何话。只是将一个沉甸甸的画箱,递到了阿萦的面前。
正是那个一年前,被他亲手收走的、属于她的画箱。
“山上的活儿,还很多。”王道玄的声音,有些沙哑,却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将作监那边,前日下了新的文牒。宾阳洞那尊被裴侍郎斥责过的菩萨,监正大人说……就按你原来的样子,不必改了。他说,那样,挺好。”
阿萦猛地抬起头,不敢置信地看着师父。
王道玄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极其罕见的、浅淡的微笑。
“你的画,”他说,“为师,看懂了。”
他转过身,步履蹒跚地,朝着龙门山的方向,慢慢走去。那背影,在清晨的阳光下,显得苍老,却不再固执,反而有了一种与这人间和解后的安详。
阿萦捧着那只失而复得的画箱,站在原地,泪水,无声地滑落。她知道,她与师父,与过去那个分裂的自己,终于达成了真正的和解。
1 ^. T/ M, K: f3 I! N) Q* J3 ]6 m y& T/ _: f' K! ^
- M: O) P& N+ ]
作者: xiejin77 时间: 2025-8-22 08:14
拾柒& d s' }, b9 C c/ S5 r
" n. }# x( ~& }5 X. _+ A Y" a3 N故事到了这里,就应该有一个童话般的结局了。
阿萦重新回到了龙门山,恢复了她画工的身份。但一切,又都和从前不一样了。
她不再被拘束于那些冰冷的法度和规矩。她可以自由地,将她从人间烟火中汲取的温度,融入到那些神佛的仪容之中。她的画,变得愈发醇厚,愈发动人。她笔下的菩萨,既有出世的庄严,又有入世的慈悲,观之,让人心生温暖与亲近。
她成了龙门山上,最受欢迎的画工。许多来自民间的信众,会专程点名,请她为自家捐造的佛像“点绛唇”。他们说,阿萦姑娘笔下的菩萨,最“灵”,最懂凡人的苦乐。
而那幅《神都烟火图》,依旧挂在大槐树下。历经风吹日晒,色彩非但没有褪去,反而因为蒙上了一层岁月的包浆,显得更加厚重而温润。它成了“静心斋”市集,乃至整个洛阳城的一个地标。人们说,那是神都的“清明上河图”,只不过,画上的人物,都还活着。
王大娘的“半两食铺龙门店”,生意愈发红火。许多人慕名而来,不只是为了喝一碗汤,更是为了看一眼那位传说中“骂跑了侍郎大人”的、侠义的汤铺老板娘,和那幅挂在不远处的、传奇的画。
至于小乙,他依旧是那个看起来有些懒散、有些油滑的铺子老板。每日靠在棚柱上,看着人来人往,嘴里叼着一根草茎。只是,他的目光,总会不自觉地,飘向龙门山的方向。
阿萦下山的日子,变得多了起来。
她不再需要任何借口。每日工作结束,她便会迎着夕阳,快步下山。她会先去“半两食铺龙门店”,帮着王大娘收拾一会儿碗筷,然后,和小乙一起,坐在那个角落里的老位置上,点一碗汤,两个饼。
他们依旧话不多。只是静静地,分享着一碗汤的温暖,和这片人间的喧嚣。
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夕阳的余晖,将伊水染成了一片温柔的金色。远处,归鸟的鸣叫声,此起彼伏。
他们坐在老位置上,慢慢地喝着汤。
“阿萦,”小乙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很认真,“这汤,好喝吗?”
“好喝。”阿萦点点头,这是她喝了无数次的味道,早已刻进了心里。
“那……”小乙看着她,那双黑亮的丹凤眼里,映着夕阳的光,也映着她的影子,竟透出几分罕见的、少年般的羞涩,“你想不想……喝一辈子?”
阿萦搅动汤勺的手,微微一顿。
她抬起头,看着他。他的脸颊,在温暖的灯光和夕阳的余晖里,微微有些发红。
她没有说话,只是笑了。那笑容,像一朵在夜色中悄然绽放的昙花,温柔,静美,胜过万语千言。她轻轻地,将自己的汤碗,朝他的方向,推近了半分。
答案,已在不言中。
他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也没有价值连城的聘礼。它开始于一块石头,见证于一碗热汤,最后,也归于这日复一日的、平淡而温暖的相守。
阿萦时常会想,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画。
为了生存?为了师恩?为了证明自己?
或许,都曾是。
但现在,她看着眼前这个正咧着嘴、露出一口白牙对她傻笑的年轻人,看着不远处那幅融入了城市肌理的巨画,看着这满屋升腾的、温暖的烟火气。
她终于明白。
她画的,只是爱。
对这片土地的爱,对这些人的爱,对这份热气腾腾的、充满了生命力的生活的爱。
神圣存于世俗,深情藏于平淡。
这或许,就是这神都烟火,与她手中的点绛唇,最终想要诉说的、全部的秘密。
) @# r$ |% [7 ` F3 _
全文完
6 u* q) w6 L- r1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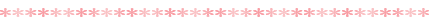 7 I! w7 ^9 t1 o
* {3 _+ s$ r2 B
7 I! w7 ^9 t1 o
* {3 _+ s$ r2 B
& @0 v% O) n$ c
作者: 喜欢就捧捧场 时间: 2025-8-22 22:27
非要选择么?小孩子才选择
| 欢迎光临 爱吱声 (http://129.226.69.186/bb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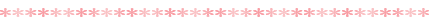 7 I! w7 ^9 t1 o
7 I! w7 ^9 t1 o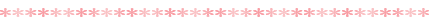 5 a! n7 U0 n: K
5 a! n7 U0 n: K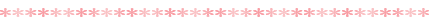 7 I! w7 ^9 t1 o
7 I! w7 ^9 t1 o